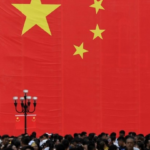写在前面:国际刑事法院对强奸的定义是:“……通过武力,或使用武力的威胁,如暴力、逼迫、监禁、心理压迫或是滥权,或利用有胁迫性的环境来对付另一个人,而对方并非真心地同意。”判断是否是强奸,核心在于有没有“违背对方的意志”。
然而当下社会对强奸的判定标准还非常苛刻,“婚内强奸”和“约会强奸”这样的概念还未被大众理解。即使是在双方都同意的性行为中,一方做出违背另一方意愿的行为也是强奸。Stealthing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指的是男性故意在性交的过程中偷偷摘掉或故意破坏避孕套试图让对方怀孕或感染疾病的行为。
2018年冬,一个遭遇约会强奸的女孩来找我求助,强奸她的男子在事后告诉女孩他有艾滋病。女孩选择了报警,我陪她全程走下来,她的沉着和勇气让我赞叹。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经历,如果让更多人读到,会更了解关于:约会强奸、艾滋预防、如何wei权、报案后会遭遇什么、如何陪伴受害者……等方面的知识。
征得她的同意,我把这个过程写了下来。为保护当事人隐私,事件细节有所调整,全文除了我的名字外都是化名。全部内容都不是虚构的,但我也无意证明它们的真实性,全凭读者自己判断吧。
1. 求助
201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微信上一个没怎么说过话的好友突然给我发了消息:
“肖美丽,我的炮友欺骗我,在我体内射精,算不算强奸。”
“算。”
“我可以告他对吗?”
“比较难”
“那我该怎么办?是我活该吗?”
“当然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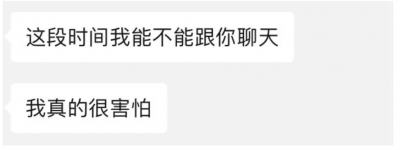
事情发生在当天下午,女孩发来了她和那个男人的聊天记录,男人说:

显然,这个男人认为——把一堆可能致孕且声称含有艾滋病毒的体液在违背他人意愿的情况下射入对方体内,只需要说几句道歉就没事了。当他发现吴菲没有“翻篇”之后,他非常怂,立刻就把自己的微信和豆瓣头像都改成了国旗,名字也改成了爱国爱党少先队员之类的。这种强奸恐吓完女人就对祖国表忠心的行为真的很值得玩味。
我决定帮她。我告诉她近期检查没有用,72小时内还可以吃紧急阻断药。她说明早有课,又撤回了那条消息,说:“都这个时候了,还想着上课。”
第二天早上吴菲跑了好几个地方,最后确定“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可以买到药。医生问她有没有钱,她说有。其实她没有,但她想再没钱也要吃药。检查费加买药一共3033元,她只有一千多,情急之下给一个表哥打了电话。她知道这个表哥也约炮,所以在这方面不会“撅”(骂)她。
我问她需不需要我去医院陪她,她说:“不用,没事了,药已经吃了,下午再查两个就好了。”我说:“我还是去找你吧,见不到人我不安心。”听到这里,她有点鼻音:“那你来吧。”
我担心自己可能把这事搞砸,毕竟我没有任何专业经验。好在我的朋友们成了我的智囊团,她们当中有律师、女权行动者、学心理的、学社工的……我在陪伴吴菲的时候,她们在陪伴我。见她之前我提醒自己——我能给的就是陪伴、聆听、把我知道的信息告诉她,不管她的决定是什么都支持她。
吴菲说她在门诊部二楼,“绿色的外套,红色的书包”。医院修得太大了,很暗,舍不得开灯似的,显得非常冷清。我搭扶梯上去,她说:“我好像看到你了,你一个人吗?”我说:“一个人。”
我第一次见到她,绿色是翠绿,红色是玫红,像是刚从颜料卷里刚挤出来的颜色。她垂着眼睛,头微微低着,扎一个马尾,头发黄黄的,很多断掉的或者新长出来的碎发从头顶不规矩的冒出来,让她看起来有点毛茸茸的。我们有一段时间的沉默,然后她说:“其实我有点内向,别人见到我都不敢相信我是那种会出来约的人。”
2. 犹豫
从为平热线那里她知道了报警可能遇到的状况。她的表哥和朋友都劝她算了,她准备回学校,我陪她去地铁站。我们走错了路,医疗中心周围荒凉极了,马路很宽,高架桥很大,树很小。
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谈到现在几点钟了,看了一下时间,她停了下来,她说这事还没过48小时,意味着现在还能取证。她身体里那些伤害她的证据正随着体温渐渐失效,她说:“万一不只我一个人呢?万一之后他对别的女生做出更严重的事情呢?至少我还能给他留个报警记录。”

最让她害怕的是报警之后警cha会传唤那个男人。她不止一次给我介绍这个男人的历史:十五六岁就组织一群小孩偷电瓶车、开过“鸭厂”(组织男性性工作卖淫)、贩过毒、嫖过100多个女人、有很多前科,现在给一些大公司卖刷流量的手机号。他知道一些吴菲的个人信息,吴菲极度怕他报复自己。
那些“丰功伟绩”在我听来有可能是被夸大的,但在吴菲眼里它们比事实更真实,它们给她造成的恐惧也比事实更真实。她的恐惧还来自她不太了解的艾滋病,以及紧急避孕药和阻断药会对身体造成的不良反应。请记住这些恐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时刻被它们包围着,有时这些恐惧还会从她身体里溢出来将我一齐包裹住。
她犹豫着,既不甘心又非常害怕,我们停在路边。我说现在医院还没下班,不然先把证据取出来,也许以后能用得上,现在想想我真是侦探剧看多了。我们问了前台、检验科、化验中心、妇科医生……所有人都告诉我们这么做没用,只有警方取样才能成为证据。吴菲还是挂了号,医生听了原因后略带疲惫的脸上多了一些愤怒,轻微的叹了口气,她知道这是无用功。
这段时间吴菲不断的权衡利弊,她的不甘心占了上风。快五点了,她说派出所要下班了,明天一早就去报警。拿病例本的时候我问医生如果明天早上去报警,还能提取出有用的证据吗?医生问:“为什么不早一点,要明天早上?”我说派出所下班了。医生说:“派出所还有下班的啊?”
医生语气强硬的话点醒了吴菲,出了医院我们就打车去了事发地的派出所。我在车上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让她把074热线做的那本反性骚扰(专题)小册子里关于报警的内容帮我念一遍,把耳机分了一只给吴菲。那段内容显得好短,但还是给了我们一些底气。
3. 报案
“报案。”派出所大厅里我只能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和心跳声:“强奸。而且那个男的说他有艾滋。”那里坐的一排警cha都是剃着平头的男人,看上去没什么差别,我就选了直线走过去的那个。他面露疑惑,我又解释了一遍。吴菲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她紧张得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说:“我们要一个女警cha”,大厅里唯一的女警被叫了过来,我有点欣慰。没想到女警撇着嘴瞪着眼,身体像一下子垮了似的,变得像个叛逆的中学生。
男警带我们到了一个小办室,他问:“你们俩谁报案啊?”我说:“她”。吴菲详细的讲了一遍事情的经过:
她在豆瓣上认识了一个炮友,有文字记录证明她要求一定要带套而且不能有传染病,男人答应了。第二次约炮的过程中,男人说没有套了,她让他出去买,男人不愿意,她说她自己出去买。结果被推倒强迫发生了性行为,她用力挣扎却无法动弹,情急之下只能大喊不准射在里面,但他还是射了。吴菲觉得自己被强奸了,非常生气,穿好衣服离开了,愤怒之下删掉了男人的微信。她买了紧急避孕药赶紧吞下,在网上搜索关于避孕的信息。得知吃药不一定有效,又把男人的微信加了回来,希望保持联系。这时男人说他有艾滋病,吴菲崩溃了。过了一会男人发了一段语音,笑着说是喝了酒,头晕,逗她玩的。
男警听了之后一边翻着吴菲的聊天记录一边问:“他为啥要说他有艾滋呢?为啥要那样说呢?”吴菲很慌张,她还在继续她的回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艾滋,我很怕,不知道他说的哪句话是真的……”我只能替她回答:“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反正他说了。”
男警问:“这个豆瓣APP是个专门的约炮软件吗?”她回答:“不是的,是看书看电影的。”男警:“那你为什么在上面约他?”我回答:“上面也可以认识朋友约线下见面的。”男警不耐烦的看着我,抑制着厌恶似的对我说:“你到那边坐一下,让她来说。”
整个经过对这位男警来说似乎太难理解了。
“他在哪儿说的艾滋喃?”
“微信上,你往后翻嘛。”
“做了事之后他把你微信删了?”
“我把他删了,因为我很气。”
“他在哪儿说的哦?”
吴菲指着微信聊天记录:“这上面啊。”
“但你说的删了得嘛。”
“删了之后加回来了啊。”
“他之前跟你说的他有艾滋?”
“他之前没有说。我觉得自己被强奸了,我很气,把他删了,吃了紧急避孕药,药不一定有效,又加回来了,你听懂没有嘛!”她哭着喊出这段话。
“不要着急嘛,我要问清楚撒。”他闭嘴看了一会儿聊天记录,吴菲一直在抽泣。
过了一会儿男警问:“他有没有女朋友喃?”
“有。”
他用手机给聊天记录拍照取证,一边拍一边骂:“日你妈的,反光。”吴菲举了一个笔记本帮他挡住直射光线。女警蹲在屋角抽烟玩手机,时不时的发出打喷嚏和噗嗤笑的声音。男警嫌要拍照的内容太多了,又骂:“日你妹,这么多。”拍完照他让我们上楼去,我才意识到刚刚不是笔录,笔录还没有开始。
4. 笔录 【第一回合】
和电视里经常出现的场景不一样,笔录不是在一个小房间里,而是在一个有十几张桌子的大办公室里进行。要在如此公开的地方问询这样的案子,这让我惊讶。
男警在尽头的一个格子间开了电脑,我们坐在他周围。女警在一张办公桌上翻来翻去,问男警那些东西能不能吃,他们贫了几句嘴。我意识到那是男警的办公位,从我们进派出所开始他们都没有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我瞄见那里贴着名牌,写着:“马于”(化名)。
办公室里除了我们还有一个在收拾东西的警cha,过了一会儿他招呼道:“我走了!”女警干巴巴的喊了两遍:“我也想走……”她的话浮在空中没着没落的。
为了说服吴菲赴约,炮友把他的身份证号发给过她,警cha根据号码调出了他的身份信息,我们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李奥(化名)。
笔录开始了,马于让我坐远一点不准说话,他把吴菲的手机拿走了。她陷入了孤立的状态,我庆幸还能坐在她身边,但大多数时候,我能给的也只是一些眼神上的鼓励。马于声明道:“我在这儿问你是代表工作上问你……你要理解。我们之间没啥的,都是结了婚的有老婆有娃娃的,给你说一下。”
笔录的过程像用钝刀杀死粘鼠板上的老鼠那样漫长,大概就是楼下的那段对话乘以1000倍的痛苦。我尽力消化和复述这场漫长的问询,但它非常的重复和琐碎,有时甚至令人抓狂,还请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准备多一些的耐心。
这是一种命令型的询问,与其说是“询问”不如说是“反问”更合适。在我看来,他提问的目的常常不是为了答案而是为了确定他的假设,有时他也用提问的方式攻击吴菲。
如果吴菲否认,他会烦躁甚至发火;如果吴菲主动回答很多内容,他会说:“大概就行,不用那么精确”。他还会吼吴菲:“不要说那么多,跟着我的思路来。”他把全过程按照他的设想重新组装了一遍,他似乎痛恨细节,也许因为细节常常证明他组装得不对。吴菲艰难地不断地纠正马于,不停地重复已经讲过的话。
“(第一次约炮)晚上发生了几次性关系嘛?”
“记不到了”
“大概几次嘛。”这个细节他倒是不讨厌。
“四次五次嘛。”
“那么凶(厉害)?”他一边说一边笑,女警也跟着笑。马于说:“我日”。
吴菲说:“你说的不能带个人感情。”马于收敛了一点。
……
“没给钱?”
“约炮又不是卖……”
他在电脑上啪啦啪啦地打字,一句话会念念叨叨地重复到打完为止。似乎有一种自动翻译软件在他的脑袋里运行着,把所有话都朝着对吴菲不利的方向调整。吴菲的拒绝他写成“没有协商一致”;她的犹豫、谨慎和担忧被忽略,他说:“对嘛,反正最后就是同意了嘛,没必要那么复杂。”看了李奥发来的照片,他补充道:“看了他的照片觉得还可以”。
每一轮性行为的时间和步骤都做了枯燥的询问,唯独到了吴菲最关注的性侵的部分,马于自然无痕的跳了过去,她几次试图把话题拉回来,得到的只是:“等于就是在里面射你有点生气嘛。”
“他豆瓣专门约炮的啊?”
“我不晓得”
“你以前约过几个嘛?”
“这有关系吗?”
“你以前约过没有嘛?”
“这有关系吗?”
马于没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嘛。”
吴菲说:“重点是我们约好带套的没有戴,说好不能体内射的,他射了。这是违背我的意志的。”马于像没听见一样。
5. 笔录 【第二回合】
后来吴菲告诉我说,刚开始做笔录的时候还因为警cha的态度而难过,这让她觉得自己的遭遇一点都不重要。后来就转变成了愤怒,她开始反击。马于又从头问起,第三轮问得更加琐碎。
“你知道他名字不?”
“不知道。”
“那咋个称呼喃?”
“不称呼啊,就像我现在也不晓得你的名字一样。”
“你不认识他?”
“不认识。”
“你不认识他为啥要约他出来发生性关系喃?”
“一定要是认识的人才可以吗?”
马于追问:“是为了寻找刺激吗?”她顿住了。“问你呢”,他催促她回答。
她的眼睛望向我,我用口型对她说:性…欲…。
她回答:“人都是有性欲的啊。”
马于继续把所有情绪都藏在烦躁里,一边在电脑上敲字一边说:“(约炮)是为了满足性欲嘛”。
性行为细节被放在有色放大镜下仔细研究,不厌其烦,就算吴菲拒绝回答他也反复问,一定要问出他要的答案。
“喂进去没有喃?”
“’喂进去’?啥子意思?”
“就是插入阴道没有嘛。”
“插了啊。”
“好长时间喃?”
“这个也很重要吗?”
“可以说可以不说。”
“不说。”
“安?”(四川话表示询问的语气词)
“我记不到了。”
“快不快嘛?”
“我不说。”
“大概好长时间嘛?”
“这个很重要吗?”
“你报强奸得嘛。”
吴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正常……”
“几分钟哇。”马于给出了他认为正常的时间长度。
“……嗯”
6. 笔录 【话剧】
终于熬到了关于强奸的关键环节,吴菲主动讲她被压在李奥身下,她在他的身体下面“板”(挣扎)。马于不耐烦的说:“等一哈,等一哈。”
这时一个男警走进了办公室,马于轻松的和他打招呼:“你还不走?”他们寒暄了几句。男警的手机响了,铃声是交响乐,他也不接,让它响了好一阵子,这间办公室瞬时变成了一个话剧舞台。
马于对吴菲:“他就软磨硬泡是不是?”
吴:“我在他身体下面板。””和马于同时说”
马:“然后你就同意了。” “和吴菲同时说”
吴:“我在反抗。””坚定地”
肖美丽:“她说的和你写的完全不一样啊。””忍不住探身插话”
马:“她一会儿要看得嘛,开玩笑。我写得不一样对我有啥好处嘛?””转头对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吴:“我在他身体下面反抗……”
马:“你莫慌嘛。”
吴:“他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我就在反抗了,你就直接说我同意了。”
马:“你咋个反抗的嘛?”
吴:“我在板”
【新来的警cha和女警大声的闲聊。】
马:“然后你就说同意了,但是要他在外面射。”
吴:“我没有同意,我没有说’好嘛’之类的,他就直接进去了,他都进去了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就只能说不能在里面射。我是吼出来的。””愤怒地”
马:“等于是你在他身下反抗,不同意是不?他就强行把阴茎喂到阴道里面去了。”
【男警和女警聊天声音越来越大】
肖:“哎,警cha先生”
马对肖:“等一下嘛。””立刻提高声音”
肖:“其他人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房间里呢?””小声地”
马:“都是警cha,都是侦察员,娃娃都两个了,有啥嘛。都30多岁的人了,有啥没见过的嘛,是不?那儿,女生还在那儿的嘛。””指向女警”
女警:“我要去上厕所。””被指后立刻说”【说完就离开房间】
马:“我说的是案子问题,又不是啥荣辱观道德观问题。””教育学生的口吻”
肖:“不是荣辱问题,是我们当事人的感受问题。”
马对着男警:“强哥你搞快点,要求你回避。”
强:“我还要收得久。等一下。你说你的,这儿都是办案子的不存在的。”【不紧不慢的整理一堆塑料袋,噼啪作响】
肖:“你们觉得不存在,万一她觉得存在呢?”
马:“是是是,搞快点。我每年办的强奸案,比你们打的出租车还多,晓得不嘛?所以说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就跟我们没见过这些一样。”
肖:“不是不是,我只是担心她的感受,对你们没啥意见。””担忧的神情更重了”
【强哥继续噼里啪啦的整理塑料袋,交响乐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马转头对吴:“那你就同意了。”
吴:“我没有同意!我咋同意嘛,是他强行进来的,他力气那么大。我就喊’不准在里面内射,’他说’好’。这就是强奸啊。””绝望而愤怒地喊”
【女警回到办公室,继续和强哥大声聊天,塑料袋声音没有停。】
马:“持续了好长时间?”
吴:“两分钟三分钟,不到。然后他突然停了。我就问他’你咋子了’?我说’你射了哇’?他说’嗯’。我就起来,一下就哭出来了,我准备穿衣服。我问他’你在逗我吗?’他说’真的’。我边穿边拿我的衣服打他,我说’你没有把我当人看。’”
马:“穿好了用衣服打他嘛。”
吴:“我穿好了咋个用衣服打他,边穿边打的。你有没有打我说的话?’我说你没有把我当人看’。””越来越靠近马的电脑屏幕”
马:“一会儿给你改。””挥手让吴坐远一点”
【强哥的塑料袋声音渐弱】
7. 笔录 【钱和呼救】
李奥承诺报销来回打车一百多的车费。第一次去吴菲只要了100元,第二次吴菲要他把避孕药的钱一起打给她,总共150元。最后他也没给,反而说了艾滋的事。这些钱成了马于关注的重点,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记录到买艾滋阻断药时,吴菲反问他:“你这下子怎么不问钱了呢?”。马于立刻拉我做挡箭牌:“在你朋友的见证下,你好像觉得我们公安对你有什么不公还是怎么的?幸好你朋友还在这儿。”我很尴尬,必须直白的解释一下:“我肯定是站在她这边的啊。”并安抚他:“语气温柔点嘛。”

吴菲购买的艾滋阻断药
因为李奥自称“嫖过100多个”还贩过毒,而且显然没有安全性行为的意识,所以吴菲认为“他是艾滋高危人群”。和性经验有关的事又一次让马于忘记了自己警cha的身份,他嘲讽这是吹牛:“说的嘛……”。并忽略了吴菲的担忧,只复述了李奥的道歉。
吴菲说:“早上十点他来骂我。说下次他睡觉再没完没了打电话给他,他就打我。然后把我删了。”马于的回应居然是:“他没骂你啊。”她说:“这不是骂我吗?非要说’傻*’这样的词吗?”
眼看要写到结尾了,吴菲想在表格最下面那栏留备注,被马于粗暴的打断:“不需要你给我说。”他又把时间拉回了性侵那一刻,质疑她怎么表现的反抗:“你为啥不呼救喃?”吴菲答:“这是他家,我呼哪个来救我?他家就他一个人。”几乎一模一样的问答重复了整整5次,外加2次描述她当时是怎样反抗的。最后他又问吴菲之前有没有过约炮的经历,吴菲说:“我不想说,这是我的隐私。”
到了马于认为可以写备注的时候,吴菲一个字一个字缓慢而清晰地说:“因为他强行内射,我吃了紧急避孕药,因为他说他有艾滋,我吃了艾滋阻断药,这些药都是对我的身体有伤害的。我希望他得到惩罚。”但马于没有打字,而是不停的让她说话“简单点”。等她重复到第3遍,马于终于开始记录。
8. 笔录 【修改】
吴菲拿回了她的手机,我们虽然坐在一起但不敢聊天,像传小纸条一样发着微信。我说:“一会儿一定要仔细的检查笔录,那是最重要的。”吴菲说:“我觉得他很先入为主。受到这样的待遇有点难过。不想坚持了。觉得没用。还会招来报复。”我夸她做得特别好:“一直思路清晰,怼得也很精彩。”她说她是学校辩论队的。我又鼓励她:“我们加油把这个流程坚持下来。会有用的,不要怕。”
吴菲想在电脑上直接检查,比较方便修改,马于坚持一定要打印出来。他说:“要喊你签字才有效得嘛,都是大学生,有点知识有点文化嘛。”让吴菲在每张打印出来的证据上签字按指纹的时候,他有种控制狂式的偏执,一定要按照他要求的方式翻页。
他说:“你看下材料和事实有没有出入,大概的,不要吹毛求疵……我希望你明白这个意思,今天不是喊你来看小说的。”我和吴菲一起看笔录,我简直不敢相信,即使这样重复、坚持和强调,关键的强奸情节还是没有被记录在上面。他实在牢固得不行。
我指着他写的那些强奸犯独白般的句子,和吴菲交换着眼神,谁敢奢望修改他的遣词造句啊。很快我又被撵开了:“同学,你喊她自己来,不要耽搁我们大家的时候,下头还有程序问题。”我问起接下来什么时候可以拿报警回执,是不是要去医院取证,他完全不提供任何信息,只让我们跟着他的安排来。
吴菲用笔改了一遍,他在电脑上修改又打印出来给她看,仍然没有把那些句子写进去,吴菲念着:“我被他压在身下不能动弹”,“我大声的喊不要内射”,再次把这几句话写在笔录的纸上。再打印、修改,终于它们被添加进去,吴菲签了字。
9. 等待
写完笔录马于似乎放松了一些,他开始和我闲聊,问我是不是吴菲的同学。我一个快30的人了,被当成18岁的同学,这侦查员当得也太没眼力了。
“你也用豆瓣吗?”
“以前用。”
“你有男朋友吗?” (掐掉后半句“有女朋友”)
“没有。”
“你在高中谈过男朋友吗?”
“没有。”
“零零后是不是都约炮啊?”(不知道他是真无知还是装清纯)
“你也约炮吗?”
“不约。” 就这样我被塑造成了一个“好女孩”,我觉得恶心,后悔为什么要回答他。
我们被带到楼下大厅,什么都没有被告知。身体的感觉回来了,我的脑袋晕乎乎的,胃饿得疼。看吴菲的样子,她应该已经感觉不到饿了吧。她说表哥从别的城市赶过来了,他是个暴脾气,她很担心被骂,同时又期待着表哥能给她一些家人和“社会人”的支持。
过了很久,马于给了我们报警回执,这张A4纸是一晚上的煎熬换回来的,而且他说一会儿要让吴菲去医院取证。我实在太高兴了,好像他帮了大忙一样的,甚至觉得他有点亲切。(不知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不是类似的感觉。)
长达几个小时的折磨,马于惊人的固执有时会让我怀疑是不是这个人有问题。但我知道不是的,2018年7月底,举报媒体人章文性侵的当事人小精灵也曾去报警,她经历的是十几个小时被当作犯人一般的“车轮式的审问”,每个细节都被反复的提及,每一句话都被怀疑,不断的问她“为什么你不反抗。”这么一对比,我们也许算幸运的,说不定部分的“幸运”要归功于警cha对艾滋病的歧视和恐惧。
吴菲的手机响了,是李奥打来的,她恐慌起来,说李奥知道了,他要来了。我们去问那些警cha是不是把李奥叫来了,他们懒得搭理我们。问了很久他们才给出了一些态度,表示确实叫了他来。李奥还在给她打电话。吴菲说她在发抖,她觉得浑身冰冷,冷得发抖。她几乎是哀求着对警cha们说:“我真的很害怕。”
我和她好像被泡在一个鱼缸里,周围的气场因为即将到来的事情扭曲变形。穿警服的平头男人们站在干燥的岸上,满不在乎的说:“你虚啥子嘛,该怕的是他。”
“我真的很害怕,一会儿你们咋保护我喃?”
“ 莫得啥子得,你想咋保护嘛?”
我问:“可不可以站到你们后头,不要让他们有接触。”
“这儿是派出所,他能做啥子嘛?”
吴菲对我说:“他疯起来我也不晓得他会做啥子,会不会捅死我。”她说话声音在抖。她还担心如果表哥到了见到他肯定会和他打起来。她高度警觉的注意着外面的光线变化,辨别每辆开过来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