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通敌活动,主要是人在北京而跟台湾和美国通信,历时二十多年。我想80后或90后,甚至70后的人,都不会理解,跟台湾和美国通个信,怎么就算是通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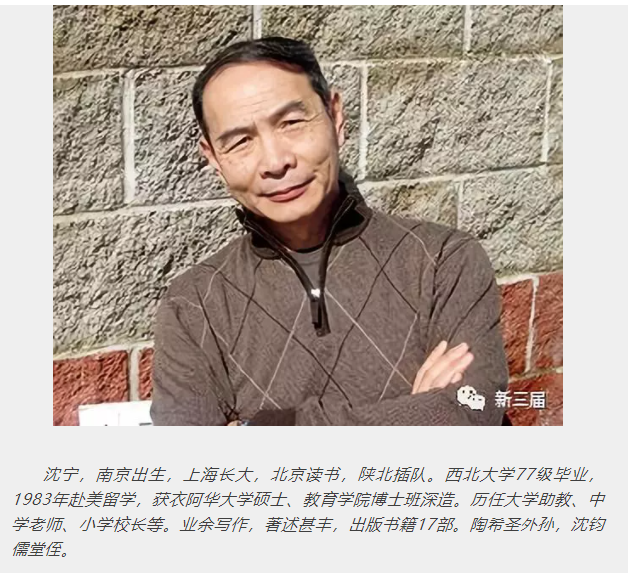
现在国内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能找出个把海外关系,时不时跟境外人士通通信,打打电话,发发微信,根本不算什么事。
可是年轻人不知道,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之后三十余年,中国大陆是绝对封闭的,国境完全封锁,天上地下,邮政电话,任何跟境外的联系,都被当作通敌。
我家的经历是最好的一个例证,值得说上一说。
我家之所以有通敌活动,先要从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涟说起。我家跟陈涟有许多关系,我的外祖父陶希圣先生跟陈布雷先生同为蒋介石文胆,是朋友和同事。我的父亲跟陈涟在浙江高中同学,后来曾恋爱一段时间。我的母亲跟陈涟在西南联大同学,转到重庆中央大学还是同学,一直是闺蜜。国共内战期间,陈涟在南京坐牢,又获释放,北上山东中共解放区,经过上海时住在母亲家。
1957年陈涟丈夫袁永熙被打成“右派”,陈涟离婚后南下。“文革”期间,我串联到上海,母亲嘱咐到华东局查看陈涟下落,才知她自杀了。陈涟为参加革命,抛弃父亲,割舍家庭,动用陈布雷车子,突破军警戒备,出生入死,给中共送情报,中共建政之后真不该如此地亏待她。
1956年陈涟夫妇尚未遭受迫害,她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提出“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的口号。她讲话之后,周恩来总理头一个站起鼓掌,于是受到中央高度关注,其讲话全文刊在《人民日报》上:
我想以自己的经验,对于知识青年,特别是社会主义敌对阵营里的儿女们的进步问题,说一些意见。也许在座的有的同志知道,我是陈布雷的女儿。
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个怀抱着热情和苦闷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途径,我找到了共产党。党把我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了社会解放的前途,我的苦闷消失了。我听党的话,工作着,学习着,前进着,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十几年来,由于党的教育,我获得了一定的进步,我现在是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着青年团中央少年儿童部的副部长。
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觉到:正是因为党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依据的,因此,它对于一切有爱国热情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是欢迎和爱护的。可是我听说,目前还有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烦恼,说什么恨只恨阎王爷把我投错了胎,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假如说在解放以前,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还比较不容易认清党的话,那么在今天,党就像太阳一样,普照着大地,抚育着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只要我们选对了方向,而且肯于努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是有宽广的道路和远大的前途的。
读到报纸上刊出的相关报道,母亲联想自己,曾想找陈涟倾诉愿望,但是没敢。父亲告诉过她,我们没有举家北上之前,父亲先调北京,外文出版社为表示重视知识分子,给父亲发了一张票,十月一日到天安门看游行。父亲在观礼台意外碰到初恋情人,陈涟先一惊喜,随即转变态度。两人寒喧几句,估计因为政治立场的考虑,陈涟表示十分冷淡。
母亲听了这段故事,知道自己无法见到陈涟,便决定给周总理写信。周恩来跟我外祖父的渊源很深,可以说从1924年就开始了,当时外祖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跟恽代英、沈雁冰一起从事共产党活动,直接由周恩来领导。后来几十年,两人分道扬镳,有时笔战,有时说笑,仍旧是朋友加敌人。
母亲的信发出后,过了一阵子,忽然一天,大门口慢慢踱进一个人,问沈苏儒、陶琴熏住在哪里。父亲正坐在廊下看报,赶紧站起,把来人迎进屋子,让我们叫他海澜伯伯。
海澜伯伯是个文人,非常儒雅。他站在房间中央,左右看看,出口道:小院芳菲入画图,窗明几净碧纱橱,闲来还读圣贤书。父亲一听,立刻服气,点头称赞。母亲让阿姨把我们兄妹三人带出屋子,再把两间屋子门窗都关紧,然后和父亲两人陪着海澜伯伯在里屋谈了半天,才送他走了。
之后,母亲把我和弟弟叫进里屋,很严肃地告诉我们,海澜伯伯是周总理办公室的特派员,跟父亲母亲有事商量。他来家里的事情很要紧,也很机密,我们对谁都不能讲,老师校长同学,谁都不可以告诉。
过了几年,我长大些,母亲才详细告诉我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海澜伯伯首次来访,告诉父亲母亲,母亲写的信,呈到周总理手上,周总理看了,认为母亲信中所说有道理,认为对外祖父的统战工作可以做。所以周总理任命海澜伯伯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协助母亲建立跟外祖父及海外家人的通信联系。
父亲母亲同海澜伯伯商量的结果,是通过香港,转信到台湾去。母亲原以为大舅还在香港办印刷厂,海澜伯伯通过香港地下党了解,大舅早已搬到台湾去了。母亲又想出一个可靠的关系余启恩先生,母亲一家跟余启恩夫妇有很久远的关系,在重庆还曾经是邻居。母亲认为,如果她把信寄到香港,请余启恩先生转寄台湾,应该没有问题,台湾回信也可以用同样的走法,寄回北京。
海澜伯伯告诉父亲母亲,台湾当局缉查匪谍很严厉,从香港寄信到台湾,也会受到检查。为安全起见,香港寄去台湾的信,最好不直接寄给外祖父,免得给外祖父招惹麻烦。母亲便想到,在台湾可以请阮继光代收。母亲的远房表兄阮继光,跟随外祖父作文书,是国民党普通职员,只身一人跟着外祖父去了台湾,他的太太留在湖北。有信从香港转到台湾,寄给他,应该不会引起怀疑。
海澜伯伯认为这办法可行,他会通过香港台湾两地的地下党,得到余启恩和阮继光的通信地址。写信程序是,母亲先起草信稿,交总理办公室审查,通过之后抄写清楚,然后寄出。
当时北京全城,只有前门邮局一个地方可以投邮寄往海外的信件。实际上,所有到前门局投寄海外的信件,也都先送公安部或统战部检查,获准之后才寄出,没有批准的信件就扣留。这样的作业,对外并不宣告,但中国人自己心里都十分清楚。
海外寄往国内的信件,也同样处理。到了中国邮局之后,首先送公安部或统战部检查,获准的信件就递送给国内收件人,不被批准便扣留。通过检查国际信件,公安部和统战部也收集到国内人的海外关系,决定是否可利用,开展统战或谍报工作,以及如何对这些海外关系实行监控。
海澜伯伯说,他会去邮政总局备案,母亲寄往海外的信,因为已经总理办公室批准,所以不再需要经海关或公安的检查,可以直接寄出。而海外寄给母亲的信,也不转送公安部或统战部,而是直接上交总理办公室,然后由总理办公室转交母亲。母亲收到海外来信后,自己抄一份留底,正本交还总理办公室存档。对于总理办公室而言,母亲的海外通信是一项政治工作,并非私人通信。
一切都安排好了,海澜伯伯告诉父亲和母亲,周总理特意嘱咐,这件工作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就是说,母亲只与海澜伯伯一人联系,接受海澜伯伯一人领导,不可以让第二个人知道内情。母亲要找海澜伯伯,可以写信亲自交到中南海西门,请大门警卫们转送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如果有事情要找母亲谈话,海澜伯伯便亲自到家里来。海澜伯伯开玩笑说,我们这是在通敌,所以必须保密。
从此之后,海澜伯伯经常来,有时是晚上,有时是礼拜天。每次来之前,都是先给母亲办公室打过电话,让父亲母亲在家等他。海澜伯伯总是笑呵呵地走进院子来,好像普通熟人一样,然后跟父亲母亲关起门来,在里屋谈半天话之后才走。父亲母亲从来没有参加过革命,对于海澜伯伯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以及从事通敌活动的从容和细密,非常佩服。
我头一次陪母亲去前门邮局,是帮助母亲给外祖父寄生日礼物。母亲买了几件景泰蓝瓷器,邮寄需要用木盒。邮局寄包裹先要检查,然后当面钉封,母亲不会钉木箱,所以要我跟去。
因为是设置为国际邮政,而当时北京城里普通百姓没几个人使用国际邮政,想跟海外通信也没那份胆量,所以前门邮局面积很大,却完全空旷。地面干净得可以照见人影,好像从来没有人在上面走过。我和母亲是唯一的顾客,穿过厅堂,听着自己脚步的回声,心里很害怕,觉得身后一直跟着人。柜台很高,玻璃窗洞很小,从外面几乎看不见里面的店员,我想那些店员一定都是海关的公安。母亲经常来,熟悉业务,而店里也列着母亲的名字,双方都无需多废话,手续办得很顺利。
就这样,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最森严的时期,由周恩来亲自安排,连续多年,母亲经常写信给在台湾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同时,她也经常收到香港转到北京的来信,有的是阮继光写来的,有的是在美国的舅舅们写来的。
母亲知道,外祖父身为台湾国民党高层,亲笔写信给人在大陆的女儿,恐怕还是有许多危险和顾虑。但是如果没有他的许可,阮继光和舅舅们,绝对不敢擅自给母亲写信来。而从这些来信中,母亲了解到海外亲人们的种种情况,知道她的信确实交到了外祖父的手里。
有一次母亲收到外祖母亲笔写来的回信,还有一次母亲在回信上看到外祖父亲笔署的几个字。因为海外有回信,对总理办公室来说,母亲的这项工作,就算是有成绩,获得肯定和保护。
从1956年开始,中间1966年和1967年中断过两年,然后1968年又恢复。即使母亲戴右派帽子的1957到1959两年,或是1968年后最残酷的文革几年,我家的通敌活动仍旧一直继续着。母亲为了保持跟海外亲人的联络,为了表达自己的亲情,确实非常英勇,置自己生死于度外。到1976年终于晴朗的秋天之后,海外关系的高压渐渐减轻,母亲的活动才在组织上公开,并获肯定,北京市政协委任母亲作市政协文史专员。1978年母亲逝世后,骨灰被安排进八宝山革命公墓。
为了让母亲跟海外通信时,多一点经历说给台湾的家人,总理办公室经常给我家送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当时北京,几乎所有社会活动,都严格控制,普通百姓无缘参与。从孔老夫子一套君臣父子开始,中国人历来讲究社会等级,穿个衣服,吃个饭,坐个车,见个人,都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那些限制人参加的社会活动,当然更不例外。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落成,每年五一游园会和十一焰火晚会,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票从不公开出售,都是组织上发。
1957年母亲被打成“右派”之后,由于国际部编译处领导的一力维护,没有被赶到外地去劳改。父亲写了小字报,连连只做了很多次深刻检讨,才算没有戴上帽子。母亲顶着右派帽子,还是能够继续通敌。
1959年反右倾之后,海澜伯伯不再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跟着彭德怀遭了秧。之后再到我家来接头的,换了一位王业松叔叔。他不是总理办公室的人,而是统战部的,也就是说,我家通敌这个工作,转由统战部领导了。
“文革”发生之后,母亲的家庭出身被公布到社会上,胡同里的人都知道了,附近学校红卫兵头一次来抄家,把母亲吓坏了。她并不心疼家里被捣坏被涂抹的字画文物,或者被抢劫一空的珠宝首饰,或者被撕毁被扯碎的西装旗袍。她担心得要命的,是怕红卫兵发现她保存的多年与海外通信的各种草稿和备份。幸运的是,红卫兵们虽然六亲不认,却也愚蠢无知,他们只晓得去翻封面上印字的东西,却把无字的黄封套丢到墙角,只踩几个脚印,不再理会。
红卫兵们走了之后,母亲马上收拾起那个大封套,叫了我陪同,柱着拐仗,一步步走去中南海。那天北京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正组织静坐示威,誓死揪出刘少奇,府右街坐满革命小将,交通断绝。《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歌,在高音喇叭里一遍遍地播放,撕裂人的神经,震碎人的心灵。
我搀扶着母亲,在人缝隙中走过,心里十分恐惧。可是有惊无险,什么都没有发生。马路上革命派,胳臂套着红箍,头脑全部白痴。
到了地方,母亲绕过大大小小的红卫兵头头,走到中南海西门口。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没有动,门里走出一个军官,迎接我们。母亲告诉那军官,她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经常来这里递送材料,每次都确实送到总理办公室,她很感谢。说完,母亲从我背的书包里取出大封套,双手递过去。那军官接过,看看封套上母亲写的收件人名,显然知道是谁,便向母亲保证,材料他一定会立刻交进去,让母亲放心。
母亲再次谢过那军官,我们就转身离开。那些红卫兵,看见母亲跟中南海里出来的人交谈,递送材料,也看到那军官对母亲点头微笑,猜不出母亲是何等身份。我们顺着马路往回走,坐在地上的红卫兵们都纷纷后退,给我们让路,眼睛里流露出莫名的羡慕。权力崇拜养育出这样一批畸形革命者,半面是穷凶极恶,半面是奴颜卑膝。
忽然一天,统战部给母亲送来一封信。里面是台湾《联合报》上一张讣告,我的外祖母万冰如于1975年9月2日在台北逝世。讣告是9月7日刊出,中央统战部看到,派通信员送来,已是9月18日。母亲看到,痛哭很久。
到了晚上,母亲决定给外祖父写信,命我次日一早送统战部,立等批示,当天往前门邮局发给美国的舅舅们转呈外祖父。母亲坐在灯下,费尽心血。她既要真诚表述自己的哀念,又要适合统战部的政治意图,免被打回重写浪费时间。最后母亲在信里这样写道:
父亲大人:
今天突然获悉母亲大人已于九月二日下午二时三十分病逝台北,我和苏儒感到万分震惊和悲痛。母亲的一生,是劳累的一生,痛苦的一生。她老人家几十年来勤俭持家,辛辛苦苦,把我们几个姊弟抚养成人。在我童年的时候,她克服种种困难,使一家人摆脱贫病交迫的威胁。抗日战争时期,她携带一群子女,在日寇的刺刀和轰炸下逃难,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在您遭受危难的关键时刻,她老人家不止一次地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把您拯救出来。这些惊涛骇浪,将她这样一个旧式贤妻良母,锻炼得十分刚强勇敢,但却自然地毁坏了她的身体健康,四十岁以后就不断地忍受多种疾病的折磨。现在她老人家永远安息了,人间的痛苦不能再折磨她了。然而,她直到临终,还怀念故乡,可见二十几年来旅居异乡,她的心却一直是和故乡亲人们连在一起的。我是她唯一的亲生女儿,从小得到她老人家疼爱。这些年来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她老人家回故乡,同家婆,伯娘,四干,五舅,六舅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晚年。但是,这个愿望已经不能实现了。母亲已经跟随伯娘、四干,与世长辞了。甚至在她病中,我都未能伺奉她老人家几天,尽尽我的孝心。为此,我确实万分愧恨,只有祈望她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宽恕我的这一最大不孝。
女 琴熏哀上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
母亲自1966年病倒,顽强挣扎了十二年,终于还是扛不过去。1978年,她的病情突然恶化。那时我家住东单,为就医方便,父亲找二伯伯沈钧儒的孙女沈瑜大夫介绍到北京医院。托天之幸,正那时候,海外关系突然摇身一变,从臭狗屎升成香饽饽,母亲又有了被利用的价值,于是她被安排进单间特护病房。中央和北京许多部门,又是电话又是派人,连番不断给北京医院施压,要求他们尽一切可能,抢救母亲的生命。
可是母亲没有熬过去,终于离开了她十分热爱却一直不被接受的祖国。她去世后第三天,我们接到五舅来信,说几个舅舅决定接母亲到美国治病,已经开始办理移民局手续。我把五舅的信,放在母亲的遗体上,一同火化,让母亲带着海外的深厚亲情升入天国,永不再与她挚爱终生的家人们分离。
母亲去世后,北京市政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香港《大公报》发讣告,舅舅们看到,不敢透露给台湾的外祖父。可外祖父一生主导文宣,人脉遍地,哪里瞒得过。白发人送黑发人,外祖父暗自哀伤,独坐灯下,手书一诗,名为《哭琴儿,念燕儿》:
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
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
注:琴熏儿病逝北平,近始获确息。所遗男儿二,女儿一。小女燕儿既失学,又丧母,何以为生?怜念之余,口占如右。
中国大门敞开之后,海内外的联络不必再像过去一样做地下工作,但我还想提一件小事。1982年春我大学毕业,申请美国留学,获得入学许可。可是申请护照遇到麻烦,跑了很多趟,始终不成功。最后父亲只好又去找马叔叔,转述海外舅舅们希望亲耳听我讲述母亲后半生经历和何以英年早逝,请求得到组织帮助,办理护照。于是我忽然之间就拿到护照,顺利出国,那大概是我家通敌二十年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