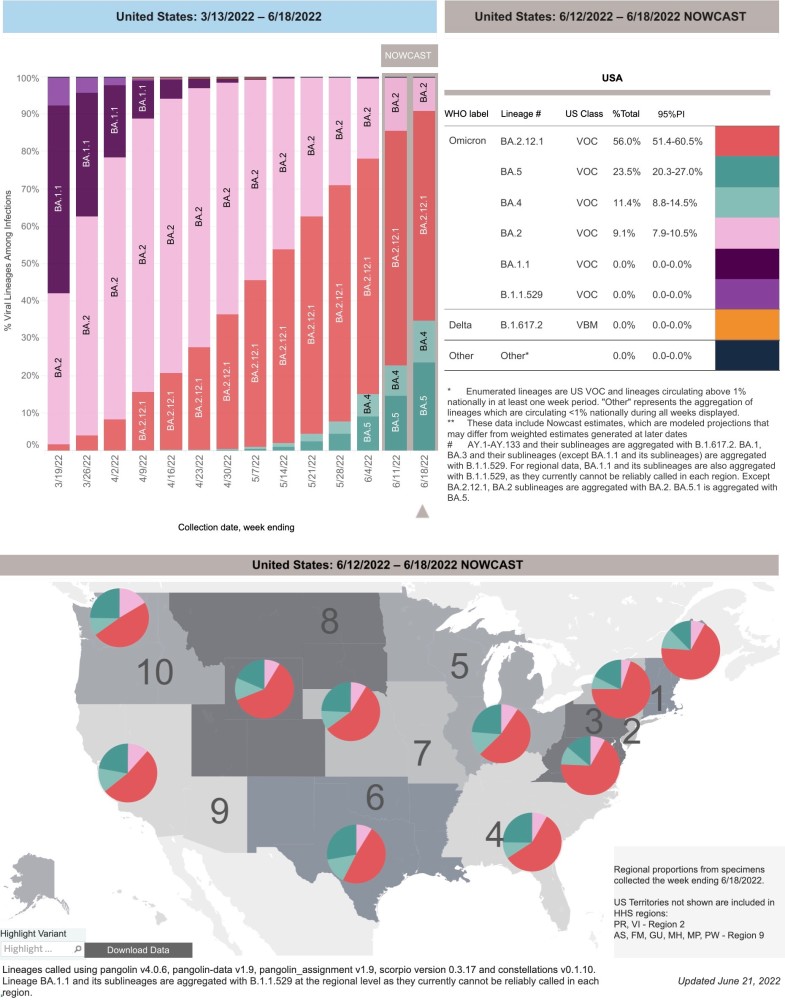在武汉出生长大的中国90后屠龙一度认为,只要他不发表任何政治敏感言论,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按照当局者的意愿做个顺民,像周围很多人一样,当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人生就会一路向上。

一场冠状病毒疫情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屠龙说,他不想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我知道这个政府有多么混蛋,” 他说,“我以前只是跟自己说不要去在意一些事情。”
屠龙是化名,尽管他同意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但他依然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从激进少年到“温水煮青蛙”
现年26岁的屠龙是在“防火长城”背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中的异数。
他说,自己11岁就学会翻墙上网,看过89六四的纪录片;在维基百科上读当权者禁忌的历史;从外媒的报道中认识一个未经审查者过滤的中国。
“毛泽东就是杀人的屠夫,”15岁时他在家里对爸妈说。
“先富起来的无非是赵家人,我们只是燃料而已,”他和要好的同学说 。
父母告诫他不要去外面发表这种言论;朋友劝说他:“好好读书工作赚钱,以后有机会赶紧离开这里。”
还在上小学时,屠龙就希望离开中国。中学时,他拒绝入团,不愿“向他们的政治靠拢”。
但是屠龙家的经济条件一般,父母无力供他出国读书。16岁时,他意识到,要在中国生存下去,他必须作出妥协,保护自己,不去以卵击石。
“OK,我按你们给我的要求,不去做这些敏感的事情,”他说。“我跟着你们走,行吧。”
屠龙的梦想是当一名记者,他努力学习,考上了全中国顶尖的新闻专业, 但他很快发在这个梦想在中国无法实现。
“我的学校就是他们专门培养控制舆情的学校”,他回忆说。“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我们老师沾沾自喜地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控制舆情的。”
毕业后,屠龙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公关职位。虽然要交很多税,虽然买不起北京的房,可是温水煮青蛙,日子久了,他觉得一切似乎也并非那么不可忍受。他告诉自己,再努力一点就能成为中产阶级。
他依旧谨言慎行,远离政治,只是很偶尔地,会在朋友圈里隐秘地表达自己的不爽,比如他会写:有一只黄熊正在开倒车;又或者,他借用昔日毛泽东、邓小平的言论来反讽现实。
“我们会故意地正话反说,”他说,“我们年轻人管这种人叫‘阴阳师’。”
不愿再沉默
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打破了这一切。屠龙说,要不是自己会翻墙,要不是一些海外的朋友告诉他真相,此刻说不定他已经进了焚尸炉。
封城的日子里,屠龙反思了很多:
“他们清理北京低端人口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很努力,我不是低端人口,我不会被清理;他们在新疆搞劳改营的时候,我想我也不是少数民族,我也没有宗教信仰,我也不会被清理;我很同情香港人的遭遇,但我觉得我也不会去上街,不会抗议,所以也跟我没关系。这一次事情发生在我的家乡,我周边已经有很多人得了病,也有去世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
公民记者李泽华对屠龙的触动很大。李泽华也是90后,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曾在中国国家电视台做主持人,后成为一名自媒体人。
2月6日,李泽华进入武汉报道疫情,探访了当地社区、殡仪馆、火车站等地。20天后他被国安追捕,至今下落不明。他是继陈秋实和方斌后,第三位“被失联”的公民记者。
屠龙说,和李泽华一样,他也不愿再沉默下去。
“这件事情被瞒报了整整一个多月,”他说。“事情发展到今天,不仅没有人出来给武汉人道歉,他们还告诉我们要去仇恨美国,我们应该去仇恨日本,我们应该去仇恨韩国,我们应该去仇恨台湾,我们应该去仇恨《华尔街日报》,没有人出来为这件事情买单。我们‘伟大的’市长周先旺前几天还被中央公开表扬了。
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治愈,我们已经把它当成喜事了。《大国战“疫”》都已经出版了。太荒唐了。”
“太荒唐了!”他又一字一顿地说。
一场“人性的大考”
除执政者外,很多中国民众的言论和做法也让屠龙失望。 有位同学的妈妈染上新冠肺炎,因为没有病床在网上发帖寻求救助,立刻就有“小粉红”蜂拥而至,要求删帖,还说他是“被境外势力控制”。屠龙本人也常被人说“被外媒洗了脑”。
“说实话,这件事情给我刺激最大的,真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人性的大考,”他感慨道。
屠龙曾经一直对他在海外的朋友们说,你们要把“中共”、“中国”和“中国人”分开来看,可是这段时间他告诉自己,“没有办法分开”。
“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并不无辜。因为我们纵容了他们作恶,当然还有更多人是跟他们一起做恶, ”他说。
他又说:“现在中国弥漫着一种不寻常的乐观气息,我看到报道说,全世界欠中国一个道歉,甚至说什么没有这次新冠肺炎,我都不知道中国这么牛。现在,武汉还在牺牲,还在受苦, 他们还跑出来说,哎呀,你看现在国外做得多么不好,就是我们中国做得特别好。非常可怕!”
准备“逃难”
屠龙已经辞去了北京的工作。疫情结束后,他希望离开中国。他说,自己不是游学,也不是移民,而是“逃难”。
之前曾有朋友对他说:想要在中国生活下去,有两点你要做到其一,两个都做到是最好的——第一,丢掉自己的理智;第二,丢掉自己的良心。
屠龙觉得,这两样,他都做不到。
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次事件我熬过去了,我幸运;熬不过去也是一种解脱,但是只要我熬过去了这件事情,作为武汉事件的幸存者,我这辈子有义务为死去的人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