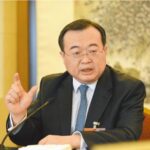不结辫发的华人
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十月,福建与广东的总督巡抚以联名方式书写奏摺,上呈雍正皇帝。这是根据兵部的咨文,对雍正帝上谕的回应;皇帝在上谕中,指示要检讨海外华人的归国措施,并且呈送康熙年间海外事务的相关档案,以供对策之参考。在这份奏摺中,督抚们报告了透过传闻得知、关于巴达维亚(雅加达)和马尼拉的情势。在报告里他们说,巴达维亚方面的华人一定要剪去辫发,而在马尼拉则是没有剪去辫发的必要。从这点可以证明,清朝当局对于海外的反清活动相当敏感。
福建、广东的督抚们提议,让有能耐的人化身为贸易商人,又或者是从干练的贸易商人中挑出适当的人选,将他们派往巴达维亚与马尼拉,让他们去刺探“在那个国家有何动静?定区当地的内地人(华人)实际上有多少人?在那块土地上做些什麽事?让中国人居住在该地有何意图?”等事项。对此,雍正帝批下硃批:“说得简单,要获得人才却很困难。若是没有谨慎行事,以大大的厚赏作为鼓舞,且慎重挑选人才的话,这些(清朝派出从事秘密侦查的)人们将会惊动对方的国家,反而会比派遣官员更打草惊蛇吧!要仔细地挑选人才去进行。(言之易,得人难。非十分留心,大设赏鼓舞,慎重其人,则此人之惊惶彼国,而反甚于遣官也。详细择人为之)”
雍正帝在硃批中,清楚表明了以下的担忧:相较于长崎的不同状况,将密探送进荷兰、西班牙支配的地区,恐怕会引发外交纠纷。纵使解除了南洋海禁,清廷对这些和西洋各国有关的地区状况,依旧抱持著强烈的警戒感。
从笔者迄今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尚无法判断清廷在这个时期,是否真的派出了密探。不过,督抚们基于风闻上报、有关爪哇与吕宋华人社会的情报,既是当事者共享的资讯,那跟现实的状况,想必不会相差太大。在雅加达方面,“米穀的价格极为低廉,工艺匠人们也容易获利。因此,人们(剪去辫发)蓄发定居,结婚生子,丝毫没有想要回乡的心意(米穀甚贱,工艺之人,易于获利。是以蓄发居住,婚娶生育,竟不作故土之想)。”在良好的经济环境之下,有助于汉人在当地的定居及发展,“关于管理汉人方面,当地政府以汉人为长,赋予『甲必丹』的称号,当有诉讼之事发生时,便交由他们审理。同时也会发给每个人身分证明,方便盘查(至管束汉人,即以汉人为长,名曰甲必丹。凡有讼事,归其审理。每人给照护身,以副盘查)。”上述具体呈现了当地华人社会的成熟程度,甚至已经具备自治机构。
但是,对于当地华人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与安定生活,清朝当局不只未曾遥寄祝福之意,反而益发增强了警戒心。在解除“南洋海禁”的前后时期,清朝所采取的对应,是接二连三强化了对海外渡航者的管理,并且实施强化限制从海外归国的政策。这就是对带有自律性的海外华人社会扩大之事,怀有警戒心的表现。

被团团包围的唐人
相较于南洋方面,清廷对于长崎的状况,较能获得具有高度可信赖的情报。正如松浦章所论述的一般,康熙帝在一七〇一年(康熙四十年,日本元禄十四年)派遣内务府司库──也就是经济官僚──莫尔森(又称麦而森),作为密探前往长崎。
莫尔森出身包衣世家;“包衣”原意是皇室的家奴,不过经常可以看见飞黄腾达的包衣,以皇帝心腹的身分活跃于蒐集情报的任务上。莫尔森所带回的情报,其详细内容不得而知。但是,当时清廷仍对日本抱持著强烈的警戒心;有鑑于和日本相关的情报真伪混杂交错,莫尔森的使命,便是对这些情报进行确认。从长崎归朝的莫尔森,表示那些是“假捏虚奉之词”;他的说法似乎给予康熙帝一种印象,那就是当时的日本“懦弱恭顺”,在对外政策上相当消极。据雍正帝说,康熙皇帝因此解除了对日本的戒心,“嗣后遂不以介意”。
关于长崎,正如众所周知一般,浙江总督李卫透过密探、以及对浙江方面归国者的询问,获得高度精确的情报,并将之向雍正帝逐一进行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带回来的情报显示,那些应日方要求,渡航前往长崎的医生、军人、知识分子、制造武器的工匠等,在当地从事活动的情况固不用说,就连一般的贸易商人,也被置于严格的管理下,几乎被剥夺了行动的自由:
凡平常贸易之人到彼,皆圈禁城中,周围又砌高牆,内有房屋,开行甚多,名为土库,止有总门,重兵把守,不许出外间走得知消息。到时将货收去,官为发卖,一切饮食妓女,皆其所给。回棹时逐一销算扣除。交还所换铜觔货物,押住开行。
(译:一般的贸易商人到了那个地方,便会被圈禁在城中。城镇的周围砌起高牆,内侧有家屋,许多商人就在住宿处开起了店铺[行]。这样的建筑称为“土库”,只有一扇大门,外有重装备的士兵守卫,不许随意出外閒晃、打探消息。抵达之后的货物也会被收纳[进仓库],由官方代为贩卖。所有[中国商人的]饮食与妓女,都由[官方]供应,在返航时逐一精算扣除,当作付款;至于[作为代价]得到的铜料和货物,则会被押送到商人住处。)
在这里称为“官”的,必须是通事和商人中的“乙名”;然而,通事和“乙名”虽是被拔擢为“御用”的城镇公务员,但不是真正的“官”。因此,“信牌”的发给是挂在唐人通事名下,也就是说,他们具有给予中国商人“信牌”的地位和权限,因此在他们背后,可以隐约见到奉行所的权力。此外,令人深感兴味的是,从被严格管理的中国商人角度看来,唐人通事的形象,基本上和“官”是相互重叠的。最后,就长崎贸易而言,将贸易对象的中国人、荷兰人置于隔离状态的政策,并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一七〇一年康熙帝的密探莫尔森,应该也有被关进唐人馆的经验。
再者,李卫的长崎情报,应该也是透过贸易商人听取得来的,其中将唐人馆内的建物称为“土库”这点,也让人颇感兴趣。所谓“土库”,原本是指以土石建造起来的仓库等;这个词彙藉由福建人的贸易商和移民,逐渐普及于东南亚,不过这里是转变为指称作为贸易据点的商馆之意。在张燮《东西洋考》卷三,关于下港(Banten/万丹)的记述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其贸易,(万丹)王在城外开设两个涧(似乎是市场之意),设置店铺。一到凌晨,人们便前往各个涧进行贸易,至正午结束。王每天徵收税金。来到万丹的荷兰人(红毛番)所建造的土库,位在大涧东边。葡萄牙人(佛郎机人)所建的土库,位在大涧西边。这两种夷人皆是以哈板船,年年往来于此(其贸易,王置二涧城外,设立铺舍。凌晨,各上涧贸易,至午而罢。王日徵其税。又有红毛番来下港者起土库,在大涧东。佛郎机起土库,在大涧西。二夷俱哈板船,年年来往)。”
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造访巴达维亚的王大海,在其见闻录《海岛逸志》中有“在巴达维亚贸易的人,大家都接受土库的待遇(土库是巨大的家屋),交易也是遵守巴达维亚的约定(在吧贸易者,皆处以土库[巨第也],其交关亦遵吧国约束)”。许云樵《南洋华语俚语辞典》中解说:“在闽南,将『栈』称之为『土库』,现在则是指外国人的商品仓库和商行(闽南称栈曰土库,今指外人货仓及商行)。
“栈”所指的就是“货栈”、“行栈”、也就是贸易的经销批发商;他们为从事商品买卖、不辞千里自远方而来的客商,提供住宿、买卖仲介、代理等服务。在广东省东部潮州的商业港口樟林,外洋船隻从事贸易的“洋船栈”,“多数是巨大的建筑物,将商场、仓库、住宅、客舍连为一体,占地一亩(约两百坪)左右。因为邻近港口,唯恐涨潮淹水,而采多楼层建筑(多数是巨型的建筑,每座联商场、仓库、住宅、客舍于一体,占地约一亩左右。因邻近港旁,涨潮内涝,均可为患,故都有楼层)”。即便到了现在,在马来语系的语言中,toko也广泛被使用在意指“商店”的语彙上。长崎的贸易商,将唐人馆内自己宿泊的家屋称呼为toko,应该是由于他们认为其与中国的“行”、“栈”具有相同机能的缘故;这也显示,长崎贸易是扩展到东南亚方面的唐人贸易网络中的一部分。

华人的利用与管理
李卫提醒皇帝注意,信牌制度可能会成为日本用来逼迫中国商人、实现种种要求的有力道具:
数年以来设立倭照,挟制客商。始则要求礼物,继则勒带人质。遂多干犯禁条,不一而足。
(译:数年来,[日本]设立倭照[信牌]制度,挟制客商。从要求礼物开始,接著便开始强制要求带入人员和货物,结果导致许多违禁状态出现。)
长崎当局在实施信牌制度的两年后,开始使用信牌,作为获取愿和日方合作者的利益诱导手段。其第一号,便是广南船的陈祖观。陈祖观在一七一七年(康熙五十六年,日本享保二年)八月七日,未携带信牌而来航长崎。他接受日方的要求,答应帮忙确认“四十三名船头的信牌在宁波被扣押”这一风传是否属实,从而领到了日方新发行、于丁酉年(一七一七年)来行的信牌。随即前往宁波的陈祖观在九月五日回到长崎,报告“唐国官府已经相当顺利地将信牌全数交还给船主们,各船应该会逐一入港”。携带著朝廷归还信牌的李亦贤的船隻,就在十天后入港;之后,浙江、江苏方面的船隻接二连三地来航。
不久后在中国国内,一张信牌居然以七千两至一万两程度的高价,成为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并且,开始出现以取得信牌为目的之商人,应日方要求而携带医生等专业人士渡海,前往长崎开业的状况。“商人贪于倭照(信牌)而展开贸易,一味服从(日本方面的)命令。”这种状况对清朝的安全保障而言,当然是不能坐视不理之事。;但是,他们又不能以此为理由,选择从长崎贸易撤退。李卫采用的对策是,从福建、浙江的商人中选定八位商人为“商总”,透过他们实施违禁品与非法渡航的检查,同时也采取让複数的“商总”之间,实施相互监视的制度;此制度并非强化官府的直接管理,而是委任给商人们的自律管理,雍正帝也认为“非常恰当且合我心意(甚属妥协是当)”,表示全面性地赞成。
清廷之所以会采取如此温和的对策,一方面是已经认知到,透过“信牌”展开利益诱导、打破朝廷禁制的行为已成常态,另一方面无疑也是清廷判断,这样做的弊害并不大。毕竟透过详细的调查情报,清廷也得知,日本在长崎方面并非无秩序地放任违禁品与人员的流出,而是有选择且抑制性地为之。
日本最恐惧的,是自律管理的海外华人社会在其支配范围内成长的可能性。然而,在长崎,这种可能性的新芽已被完全地摘除。被圈禁在唐人馆内的中国商人,就连粮食和妓女的供给都必须仰赖通事,在交易结束后也被要求要迅速地回国。在长崎与日本女性之间生育的小孩,也不被允许带回中国。未携带信牌的船隻会被命令立即回国,要是有打算在长崎以外地方卸货的商船,将会遭受毫不留情的火力攻击。
日本实现了如此严格的贸易管理制度的信息,经由亲身体验的商人和归国者,以及康熙帝和李卫派去的间谍,虽然陈述有点扭曲和夸张,但依然确实地传达到中国当局者的耳中。这些关于长崎的情报,相较于主要由福建、广东方面传来、以爪哇为首之南洋港市华人社会的状况,呈现极端明显的对比。对于汉人反抗始终无法放下心的清廷,在“东洋”(日本)与“南洋”之间,看到了安全与危险的分水岭。这便是为何诞生于华夷夹缝间的商业势力动态,会成为清廷关注的焦点。
※本文摘取自《朝贡、海禁、互市:近世东亚五百年的跨国贸易真相》,作者岩井茂树(いわい しげき)系日本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