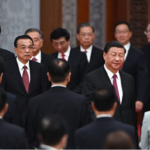中共红军一向是鼓吹“打土豪﹐分天地”﹐说穿了土豪不就是有产的农民或工人吗﹐中共红军的奸淫烧杀抢劫土豪﹐不就是奸淫烧杀抢劫一些有产的农民或工人吗。想当初井冈山上的中共红军﹐没听说种粮食的﹐那他们吃﹑穿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还不都是抢来的吗﹐不从者就烧杀奸淫﹐不也是屡见不鲜吗。要抢当然要抢那些有产的工人﹑农民呀﹔你如果无产﹐他抢你干什么﹐他不抢你并不是他对你怎么好﹐或者是代表无产阶级﹐而是他认为不值得去抢你。要知道﹐阶级其实是不存在的﹐今天是农民﹐明天可能就是工人﹐今天无什么产﹐明天可能就有产﹐成为地主﹑富农﹔今天有产﹐明天也可能变成穷光蛋。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何来阶级之说。

说“打土豪﹐分天地”是为了无产者﹐纯属异端邪说﹐既然打土豪﹐中共是不是要让你永远贫困﹐永远成不了富豪﹐因为如果你有朝一日由贫穷变成了富豪﹐中共找个什么借口﹐给你弄个土豪帽子戴一戴﹐不也把你给打了吗﹐或者你便成了该打的对象﹔或者﹐谁为了不被中共找借口把自己当土豪打﹐谁就应该永远无产﹐永远贫困。中共“打土豪﹐分天地”﹐从逻辑上分析不就是在宣传贫困吗﹐难怪四九年之后中国大陆农民﹑工人那么穷。
中共红军当年奸淫烧杀抢劫有产的工人﹑农民的情况﹐那些参与剿灭中共党军的国军将领及当时见证的老百姓是最有说服力的。中共为什么不敢让大陆人看一看这些人的回忆录呢﹐兼听则明吗。因为中共的起家史极其不光彩﹐它不敢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看到后会知道中共的政权不合法﹐土地是中共抢来的而不是中共的﹐农民有理由不向中共交纳粮食﹐那中共书记们从来不从事生产﹐不就饿死了吗﹐所以中共不敢让老百姓知道。下面我们就将中共红军当年的奸淫烧杀抢劫史暴暴光。
中共的广东暴动
国民政府人士称:
“到了下午,空气比上午紧张得多了,无理性的乱杀在各处继续进行着,据说单是在第一公园前,被残害的已经将近千人了。公园大门内的喷水池中,碧绿的清水已经变成了红色。在街头上散步,也不像上午那样自由了,武装工人像猎犬般的到处搜索杀人,在路上,一不小心就会丢去了脑袋。”
“四军军部虽未攻下,但四军军部邻近之中央银行,则于是日下午一时,即被共党占领,共党占领了中央银行后,除将行内现金收没一空外,即将银行付之一炬,自下午五时烧起,至深夜尚在延烧中。火光烛天,全城通火。时西壕口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共党虽极力进攻,仍不能胜利,不得已,乃纵火焚西关一带民房,于是到处火起,虽在黑夜,竟明如白昼矣。”
”共党所指挥的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加上很多流氓地痞,正在市各处捕人及抢夺物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现象普及全市,。。。。广州人民之无数人命财产,均牺牲于共产党之手矣,共产党之惨无人道,有如此哉!”
”共产党的残暴,素来有名。而广州暴动时,有一件最足说明中共残暴的事:原来我军各部回师广州时,共党眼见大势已去,竟不顾广州市全体人民之生命财产,欲将全广州市付之一炬,当时他们已经在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车工人,各携五加仑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在各处放火,把全广州市化为灰烬。幸我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一暴行,广州市才免于浩劫。“
红军攻陷长沙后
国民政府人士称:
”赤匪此番入城,挟其马变以后之怨毒,对长沙人肆行报复,而城内居民,因事前丝毫不知匪来如是之快,除一部分得信较早之绅富,仅以只身逃出西南两门外,十分之八留在城内;二十八日满城起火,盖赤匪对长沙绅富及党政机关服务人员之住址,早有调查,因此分头放火,抢掠财物,见人即杀。而杀人方法,亦倍极惨毒,有生剥其皮者,有投之火中者,以大刀砍杀者尚属优待。杀人最多者为梭标匪,且此时匪众多极,流氓地痞无知贫民错杂其间,大多以红布围颈,手持刀枪之属,如有荷一步枪者,已属指挥人员矣。计自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杀人在五千以上,街道河流伏尸为满。“
”共匪劫持愚民之惟一方法,为惨毒残忍,使愚民不敢不从;而匪党有其所谓阶级意识,反对封建婚姻,主张性的解放,淫欲无须避免。匪中有权力者更利用肃反以镇压异己,利用解放以实行乱交,在匪中为司空见惯之常技。“
”黄公略(红军头目之一)在湘东二年,杀人不下五万,每攻破一城,则尽掠富农商人小资产者而走,苛其刑罚,限期勒赎,但不赎固杀,赎款缴到亦杀。当长沙破城时,曾有一富孀之子为黄所执,绑之堂前树上,以荆棘状之铅丝鞭挞之,传令以十万为代价,款不到则鞭不停,富家子哀号转侧,血流满地,其母披发奔走,竭一日夜之力,勉足十万亲捧至总司令部赎子,则已成一血肉縻烂气息早绝之血尸矣!富孀哀号一声亦死。黄除杀人外,又好色纵淫,所掠大家闺秀无幸免,拒之立以大刀碎割,顺之则数日后赏其卫士为公妻,卫士人多,往往不终朝已蹂躏死。黄之残杀,比诸张献忠彷佛似之。“
中共祸乱下的湖南
国民政府人士及工人、农民称:
农人说﹕”我与我的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的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使他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工作忙得很,偏耍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
”长沙的理发店,素来由店东担付房租水电以及毛巾肥皂香水等等的设备的费用,理发工人的食宿,也由店东担负,而理发工人只贡献劳力与技术。分起账来,店东得十分之四,理发工人得十分之六,与其他商店工厂的店员工人按月计资,是不相同的。他们店东与工人之间,历来如此相处,相安无事。自从共党掌握了长沙市的理发业工会以后,便以’工资专政’口号欺骗工人,整天要工人去开会,减少理发师很多工作时间,所得的工钱,也大为减低。“
理发师说﹕”专政!专他妈的政,开会就是专政吗?过去我们有困难,老板还可以为我们想想办法,现在工会却要吸我们的血!今天捐款支援什么前线,明日纳费帮助什么义举;工作时间减少,我们的进款也每天减少了一半;还要应付这个那个,只好坐看挨饿了!如果不遵守工会的规定,就是犯法,真使我们气死了!“
码头人力工人说:”现在从码头上下的客人,由于共产党喊出‘工人专政’的口号,谁都不敢雇我们挑行李了!旅客们都自己提着行李上下。至于商人的货物搬运,则一天比一天少。像这样干下去,我们只有活该饿死!“
”当时共党又恐怕这些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作战能力不强,离开家乡,开赴异地,难免纷纷逃亡,于是想出一个很毒辣的办法,断绝士兵逃亡回家的观念。这个办法就是放纵这些拟编组成红军,原充农民协会赤卫队、或工会纠察的队员,在各人自己家乡实行一次大屠杀,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而死心塌地的跟着共党跑。“
中共祸乱下的蜀、赣及豫鄂皖边区
国民政府人士称:
“由民众自动搜山。他们反共的情绪比中央正规部队还要坚决,因共党起来时,利用地痞流氓,杀人放火,没收财产,裹胁百姓,地方受害有切肤之痛,。。。”
“余廷襄县长找了一处破屋做县政府,连门窗都没有,城墙连根掘起。我所见过的共匪,以鄂东共匪最凶恶,比毛泽东在江西犹有过之,沿途没有人烟,黄安遍地是谷子,长得好,没有人收割。这是民国二十一年八、九月间之事。”
“我在黄安南方看到一处大宅子,共产党把大宅子内壁都打通,成为一个连在一起的大房子,然后用木条隔起以作囚牢,可以关一二千人犯,关满了便拖出一批杀死。黄安南面的庙嘴湾和王锡九村,两处有共匪设立的‘政治保卫局’,这是一种特工组织。在王村中杀人上万,我们到达时,尚有尸水在沟中流,尸臭冲天,行人不能入村。”
“我进入匪区看到百姓都是皮包骨头,可怜极了,程汝怀担任行政专员,收容难民,我太太带军眷去帮忙救济,难民饿得很久,只能先给粥吃,然后才给以干饭。”
“余在兰草渡附近,与匪猛烈作战,打得匪落花流水,丢盔卸甲,竟将共产党少年先锋队截获一大批,约计八百余儿童。年龄均在十岁至十五岁之间,籍贯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乃至华南、华北均有。余得此大批少年队后,因念此等儿童,均为失去父母之孤儿,伶仃孤苦,至堪悯恻。其受共匪之赤色儿童之组训,完全出于强迫,其良知良能的本然之善,并未泯没。于是派刘柱卿为反共少年先锋队队长,施以反共产唯物之思想消毒教育。以洗其脑,重新注入三民主义思想新血轮。并将该队分为若干组,教以木工、竹工、制鞋、织袜、缝衣、织席、音乐各种技能,久之艺术纯熟,年长者拨入部队,充当新兵。因其目击共匪残暴事实,并心伤家族骨肉被匪蹂躏,反共意识之浓厚,莫与伦比,以之冲锋陷阵,皆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云。”
“ 匪军之恐怖政策亦很厉害,凡初到或占领一地,若发现‘反革命份子’,立刻残杀。政府所派之乡镇长被杀害后,甚至凌迟尸体示众。”
“然而他(苏维埃赣东北省府主席邵式平)却欢喜玩玩女人。据说他随军到一个地方,所有的‘豪绅土劣’逃避不及的,都给他捕了起来,因为他是政治委员,所以他可以自由的处罚这些人。凡是老头子,老太婆,年青的‘豪绅土劣’地主(实则这些都是良善的人)等,一概杀,或罚作苦工。至于年轻的女人,不论未婚与已婚,都指定她们为随营服役。日里给匪众缝补,洗衣等,夜则由式平挑些好的,新鲜的去做‘特种工作’,每到一地,就将陈旧的她们换上一批新鲜的她们。陈旧的是赏给士卒,新的是留御用,。。。”
“徐匪向前,觑破四川山岳纵横,地形复杂,便于逃匿。兼之农民头脑简单,容易供其利用。于是遂由鄂西之竹谿县深山密箐便道,窜入川东之城口通江南江巴中保宁一带,展开其民众组织宣传工作。并劫粮掠城,杀人越货,弄得天翻地覆,民间畏之如蛇蝎,俨若张献忠复生再来。”
“当时通南巴人民,方新受共匪蹂躏,不堪其斗争清算打家劫舍奸淫妇女之扰,纷纷向我防区逃避者不下万余人。我更本着蒋委员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昭示,在政治方面,多用功夫,争取民众归来。一时兰草渡、观音河等地,顿改萧条为繁盛,国共两区域,气象迥别,主义之是非得失,一望而知。”
“徐匪向前流窜通南巴后,所有占领政治区划之下,俱冠以苏维埃字样,如曰巴中县苏维埃,或兰草渡乡苏维埃。但是土包子共干本身,对于苏维埃的意义,却了解不深。所谓组训民众,又出一时仓皇,根本未将苏维埃意义,使民众深刻了解。于是笑话百出,一日本军政治部拿获有奸匪嫌疑之民众审讯,问其占领他们村庄的匪头姓名,及待人民的情形如何。据答称我们村庄的匪头姓苏,不知名号为何,排行老二,一般人都称唤他叫苏二爷,凶恶异常,儿童听说苏二爷来了,就不敢啼哭。最残酷伤心的,还是奸淫妇女,侮辱之后,又将其脚砍下,堆积如山。我们的祖宗传说张献忠入川,杀戮妇女,曾经堆砌人脚山取乐,现在又是劫运重逢,老百姓真活不成了。当审讯之时,旁听者甚众,无不咬牙切齿,恨匪刺骨。”
“徐向前入川之后,因进展甚快,占据几及七县,而兵力不敷,乃用恐怖政策,杀人如麻,以资镇压。于是赤区难民纷往后方逃难,十余万众,携儿带女,沿途乞食,川北各县直至川西各县,塞满难民,秩序甚乱﹐。。”
“何况共军还要向前进攻,因要扩大队伍,广抽壮丁,自十八岁至四十岁的能耕之农都抽起走了,叫老弱来替壮丁代耕,这更使生产能力大打折扣。像这样老弱们_无法适应瘠土的生产工作,所得有限得很,自食且不足,又那有余粮来供给这样多的共军享受呢?因是共军认为老百姓私藏蕃薯或玉米不缴,而便下乡搜索,此所以引起我前面所说,乡间老妇也要拿起锄头来打死共军。于是共军连穷人也不放心,防间反侧,动加杀戮,以致杀人如麻,老弱难免。我曾于匪败退营山之次日,赶到营山城,见县政府、团防局与庙宇内之集中营遍地是尸;而在城外各村口,掩埋不深而被野狗拖出来的老百姓尸体,也到处皆是,臭气薰天。故卢作孚救济组中的好心居士们所掩埋的新匪区只三四县的民尸,便得数二十七万具。至于老匪区,则因匪据较久,民尸多已化为塚中枯骨,料理不清,真是残暴不仁,至今思之,犹令人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