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时,几位商务元老的人生也谢幕在这样的时刻,商务的命运就显得更加悲凉了。 1950年5月,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的高凤池病逝。次年偏瘫了一年多的张元济,似乎预感到生命之火将息,便自撰讣告,也预备着与世长辞。而转眼1952年元月商务董事会自选的公司经理谢仁冰,在奔波劳累中,突然脑溢血而弃世。数日之后,全国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五反运动”,在物色谢仁冰的继任时,公司中竟无人愿意代表资方出面。一切都与原来不同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公私合营
在“人民出版事业”的旗帜下,像商务一样的私营出版企业,其生存空间已是越来越逼仄,已走到绝境。 1952年2月12日,徐善祥写信给陈叔通,谈起商务的困境:“目下燃眉之急为经济问题。中图公司已积欠商务贷款二十四亿之巨。电函交驰,昨始得到复信,谓中国经济之窘,与商务相同,不特贷款无法照付,且因流动资金缺乏,非增资不可。故此惟一之来源,希望已绝。人民银行,照原约本可借款八十亿元,现虽亲借五十亿元,但沪行已得总行命令,不准放款, 历与蹉商,迄无所得。”难题何止这些,转瞬又是发薪日期,在三反期内不能拖欠分文,而且人民银行的五亿短期借款也即将到期,商务“真所谓罗掘已空,山穷水尽”。徐善祥最后说,在此“贷款无着”、“借款不到”、“旧货卖不出”、“薪工不能欠”的四重难关之中,“惟有不悼冒昧”,“肯祈婉商胡愈之署长转商人民银行总行通融借款”。
陈叔通将徐善祥的信函转给胡愈之,胡回复说:“因目前值三反运动,人民银行放款甚紧。至商务印书馆经济情况,总署在三反运动期间,更属爱莫能助。”这样,摆在商务面前的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停业;如果不愿停业的话,就只有无条件地进行公私合营。
或许,商务的董事们对于公私合营早已有心理准备。1949年,政协会议期间,张元济就曾邀请陈叔通、胡愈之、叶圣陶、章锡琛等几人,商谈争取公私合营的办法,似乎当时已感到了难以为继。
1951年底,已经预感到大限将至的张元济,写信给陈叔通说:“倘能达到公私合营,实为大幸。”次年元月,陈叔通回复张元济,商务印书馆的公司合营只是个时间问题,“三月或可能改为公私合营”。收到信后,仅过了十天,已感到体力渐差、精神涣散的张元济似乎有些焦急,便又写信给陈叔通,这封信即作即辍不知几次才写成,他说:“商务公私合营,弟亦极愿于吾身亲见之。来信三月云云,转瞬即到,然消查公股,公家尚无丝毫象征,京沪各方至今无公文一纸,未知何故?”
就在那时“五反运动”开始了,陈毅曾向有关方面打过招呼,不让商务印书馆派人来张元济这里影响他养病。虽然张元济并没有受到这次运动的搅扰,但商务公私合营的事情却被迫延迟了。直到1953年10月,张元济读到《人民日报》鼓励私人资本与国家经济合作的社论,又“怦怦欲动”。于是,张元济分别致信陈叔通和史久芸,认为“本馆改为公司合营之时机,业已来临。”并请史久芸先向出版管理局提出口头要求,予以尽先公私合营。
11月3日,商务印书馆正式向出版总署提出公私合营申请书。由于当时高等学校教学用书迫切需要成立专业的出版机构,出版总署便有意将商务印书馆改组为高等学校教学用书的专业出版机构。于是,出版总署会同高教部于1954年1月16日、1月28日两次邀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代表举行会谈,商讨出版社的名称、今后的专业方向、业务范围、组织机构和领导关系、资产负债和股权清理、人事安排、筹备工作等协商公私合营的具体事宜。
那时,张元济卧病在床,便委托陈叔通为资方的全权代表,并一再让资方代表抱定“领导被领导”的五字原则,不要提过分要求。于是,会谈很快便有了结果:商务印书馆全面公私合营,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鉴于商务在海外的影响,同时仍保留商务印书馆的名称。商务印书馆原有北京及上海两个印刷厂、以及海外机构由新机构统一管理,仍沿用原有名称,不加改变。高等教育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高等学校及中等技术学校教学用书,而商务印书馆现有的出版物,如一般科技读物、工具书、古典书籍及其他不属于高等教育方面的书籍,继续以商务的名义出版。考虑到商务的传统,新机构成立后,仍暂兼营印刷和海外发行业务。关于组织机构及领导,则在高等教育部和出版总署的领导下,由公私双方各推荐董事若干人,组织新董事会。
会谈结束的当天,陈叔通便写信给张元济:“五十七年事业可有交代,实即有了结束。以后公以文史馆馆长之例,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之例,切勿过问。”
1月29日,出版总署正式批复接受商务印书馆全面公私合营的申请,并由出版总署和商务印书馆共同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筹备处,成立北京、上海工作组,以上海工作组为重点, 核实资产,定于1954年4月1日前完成商务印书馆全面公私合营的手续。从此,一个新的商务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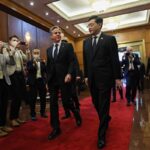




怎麼讀都不太通暢的文章,我也不曉得內容想表達什麼,有必要再重頭整理下語言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