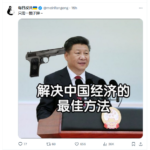夹边沟农场,是曾经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个农场,距离酒泉市区东北约30公里。最初为1954年建立的一个劳改农场,1957年转为劳教农场,1961年10月撤销,原址现为夹边沟林场。

1957年至1960年间,前后有来自甘肃省各地的三千多名“右派”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由于恰逢大饥荒等原因,大多数在该农场劳教的右派因饥饿而死亡,这一事件又被称为“夹边沟事件”或“夹边沟惨案”。
夹边沟右派噩梦:吃死人 海归科学家活活饿死
957年,中共党魁毛泽东将55万大陆知识份子打成右派。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就是当时关押右派的一个劳改农场。在反右斗争中,夹边沟的右派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3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
夹边沟位于甘肃省酒泉市30里外,地处茫茫荒漠与戈壁之间,以沙土为主,地下水60%含碱,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常常是八级大风,环境非常恶劣。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夹边沟劳教农场约有3100名被打为右派的知识份子关押在这里,他们从事搬沙填海、挖排碱沟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此外还要忍受挨饿、辱骂和毒打,身体和精神遭受着双重的煎熬。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他们只是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而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拼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1959年开始,中国境内发生大饥荒,粮食定量急剧减少,夹边沟的右派们每天仅有半斤粮食,到最后为了活命,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体面人甚至吃老鼠、吃蜥蜴,吃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三年后3000人只活下来300人。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16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三位饿死的留美科学家
饿死的右派中有三位50年代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傅作恭、董坚毅和沈大文。这些爱国知识份子,他们为了报效祖国而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怀抱满腔热情回国后,却被自己的同胞当成特务,被咒骂,被毒打,被虐待,这其中饱含了太多的辛酸与委屈。
傅作恭,山西荣河安昌村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应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傅作恭的二哥)的劝说回国从事中国的水利建设。傅作恭回国后到甘肃省从事水利工作。
1957年受“反右”冲击,傅作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傅作恭由于身体弱,完不成劳动任务,有时连续几天扣饭。挖排碱沟时由于腿部长期泡于碱水中导致大面积溃烂。
1960年冬天,傅作恭因饥饿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董坚毅,上海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兰州,在甘肃省人民医院泌尿科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1960年11月上旬董坚毅在饥饿中去世,时年35岁。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发现裹尸用的毯子、羽绒被早已不见,董坚毅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
沈大文,留美博士,甘肃农大的教授,研究植物分类。1958年被打为右派后送到夹边沟农场,在农场期间,沈大文不偷不抢,饿得不行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因他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草籽都没有中毒。
1960年春,沈大文因饥饿失去行走能力,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自己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跪着去伙房。据其室友俞兆远回忆,有天夜里约11点钟时,沈大文说想吃个糜子面饼饼。他凭借关系弄来了两个,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伸手一摸,身体已经冰凉……
右派吃树叶、晰蜴、兽骨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著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贼骨头”的生存之道
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生性本分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
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吃呕吐物和排泄物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著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
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死亡高峰到来 活人吃死人
1960年9月,甘肃省劳改局计划在高台县明水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他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著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
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1960年11月中旬,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年10月,臭名昭彰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言论自由的压制从反右开始
在反右运动60周年之际,一部记录中国右派悲惨遭遇的影片《夹边沟祭事》,2017年2月25号在香港首次公开放映。导演广州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艾晓明强调,这不仅是一个历史故事,也是一个当下的故事。
这部记录片讲述1957年,50多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很多人死于非命。《夹边沟祭事》在香港首映,引起热烈反响。
影片聚焦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夹边沟劳教者遇害惨案,并追踪遇难者的后事处理。在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后,有三千多人被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他们当时被划为右派、反革命和反党分子等。
不过,就像文革一样,反右也成为敏感历史,艾晓明多次在夹边沟拍摄过程中遭遇当地阻拦和跟踪,并受到公安和校方的约谈。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他指出对民族精英全面打击的反右运动,却被定义为反右扩大化,还用封堵的方式截断这段真相的留存,说到底,中共是不会承认它的错误。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艾晓明老师拍摄这个影片,用这个东西(记录片)来比照今日,让大家觉醒,我们什么都没有变,国家的体制,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对社会精英的敌视,对社会思想精英的敌视,这一切的一切都还是在进行着,它是党性的核心部分之一。”
胡佳:“我爸爸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被打成右派,我妈妈是南开大学的学生,也被打成右派,他们一直到66年的时候才结婚,我们这个家庭的命运,就是他们两个是右派,然后50年之后,2007年,我又变成‘右派’了。”
夹边沟
“夹边沟”本为村名,因村子的一边为被当地人叫“边墙”的古长城,另一边是排洪沟而得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解放军第三军在夹边沟开辟了一个军垦农场,并于1952年兴建夹边沟水库,后因大坝坝坡渗流,存在严重隐患而将水库废弃。1954年3月[a],甘肃省劳改部门在夹边沟建立劳改农场,行政名称为“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对外称“国营夹边沟新建劳改农场”。农场的场部位于夹边沟村龙王庙原址,离夹边沟村约有二里路程。计划将夹边沟建设成为水浇旱田作物型的谷物农场,农作物以春小麦为主,并利用农场西面天然草滩发展部分畜牧业[2]。1956年7月,转为就业农场,除了安置的刑满释放的劳改就业人员,其他犯人大多被迁到马鬃山劳改农场[3][1]。
1957年下半年,随着“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4],夹边沟农场成为接收甘肃省各地“右派”分子的劳教农场,改称“酒泉夹边沟劳改劳教农场”。夹边沟农场接收的第一批劳教人员是1957年11月初甘肃省酒泉运输公司的4人、劳改局的4人和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的48人。此后直到1960年底,陆续有3千名左右的右派分子被送到该农场接收劳动教养,具体数据各材料稍有不同。夹边沟农场环境恶劣,劳教人员过多,农场无法自给自足。恰逢全国性的大饥荒,而且当时农场管教和上级部门按照“右派就是反动派”的逻辑,未给农场提供充足的粮食,致使在夹边沟农场的部分劳动教养人员因饥饿等原因死亡[5][1]。
1960年6月,中共甘肃省委成立省农垦委员会。成立当月,农垦委员会召开河西农垦会议,提出在河西走廊开荒四千万亩。9月,中共张掖地委按上级指示,提出再新建12处农场的目标,计划在高台县明水滩新建的明水河农场就是其中一个。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通知后,除留下少数人员留守外,将其他一千九百多人全部调往明水滩。由于粮食不足,明水滩几乎没有基础设施,大批劳教人员被冻死、饿死[6]:32。
1960年11月上旬,在甘肃河西地区检查工作的内务部部长钱瑛发现夹边沟农场和明水大河农场饿死人的情况。接着,中央派出检查团到甘肃开展“抢救人命工作”,检查团以钱瑛为团长,公安部部长王昭为副团长,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等参加。张掖地委派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马长义调查夹边沟和明水大河农场,至十二月中旬将在明水滩的劳教人员接到高台县抢救,夹边沟农场也同时开始抢救人命,并开始分批审查陆续将教养人员遣返[6]:32-33。
调往明水滩的一千九百多人仅抢救回二百多人,加上留守夹边沟的、在夹边沟下属石炭沟煤矿的,以及劳教期间逃跑的等,幸存者只有五百多人[6]:33。
1962年,农场改称“红星农场”,1968年由解放军接收管理,1974年改称“酒泉地区长城机械化林场”,1982年改称“酒泉县长城林场”,1985年改称“酒泉市长城林场”。2003年,改称“酒泉夹边沟林场”,为酒泉市肃州区林业局管辖的一个生态林场[7]。
劳教人员数量
根据甘肃省甘发(64)60号文件统计,原共有2369人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其中右派分子887人,反革命分子898人,坏分子438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68人,贪污、违法乱纪分子78人。据曾在1960年底中央工作组来后被抽到高台农场成立的一个临时办公室的幸存者腊静华回忆,临时办公室统计总人数有三千多,幸存者有五百多。1958年最高峰时,农场向劳改局汇报的人数为3074人,其中女性32人。据管教人员司继才日记记载,1959年11月发放冬衣时,共有3136人。由于农场中有一些因故未记录在案的劳教人员,因此作家赵旭估计总人数应在3500人左右。劳教人员中所有死难者均为男性,女性通常会被安排到一些劳动强度弱的岗位上,因而得以幸存。[1][6]:28
农场领导
1956年3月,刘振玉任夹边沟农场第一任场长[8][b],第一副场长为王德富,第二副场长为姚世虎,教导员为申有义。1957年反右运动后期,申有义被划为“中右”调往新疆。1959年,王德富和姚世虎调到安西马鬃山劳改农场。[6]:31
1958年底,升级为县级单位,张宏被任命为夹边沟书记兼场长,梁步云任副书记,刘振玉为副场长。1959年,张宏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改在农场赶马车[9]。原甘肃省金塔县县长张和祥被任命为场长,但因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分子未就任既被撤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张宏被打倒后,农场主要由刘振玉领导,但由于刘振玉党籍一直未被恢复,所以职务为副场长。[6]:31
科室情况
夹边沟农场最初为科级单位,1958年人数增加到三千多后升级为县级单位。下设管教股(对外称教育科)、财务股(对外称财务科)、生产股、秘书股和医务所等,生产股下辖场部的三个大队。[6]:30
分队情况
1958年5月之前,全场为一个大队,10个小队。1958年6月,划分农业队、基建队、副业队;同时开始建新添屯作业站。大队长、教导员、中队长、指导员有农场管教干部担任;大队和中队的文书、统计、管理员、粮秣、司务员、上士、小队长和班长等从劳教人员中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