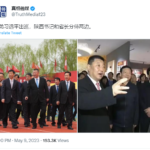夹边沟农场,是曾经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个农场,距离酒泉市区东北约30公里。最初为1954年建立的一个劳改农场,1957年转为劳教农场,1961年10月撤销,原址现为夹边沟林场。

1957年至1960年间,前后有来自甘肃省各地的三千多名“右派”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由于恰逢大饥荒等原因,大多数在该农场劳教的右派因饥饿而死亡,这一事件又被称为“夹边沟事件”或“夹边沟惨案”。
“死营”夹边沟
夹边沟,位于甘肃省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地处祁连山下的荒漠戈壁之中。这里夏天酷热,最高温度可达50多摄氏度,冬天奇寒,最低温度将近零下30度。有限的农田重度盐碱化,全年几乎无降水,主要植物为旱不死吹不折的芦草。夹边沟的生态记录告诉我们:这里根本“不宜人居”!
1957年4月,因为政治运动的需要,原夹边沟农场改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开始收容甘肃省“大鸣大放”期间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
当初,这个小型农场的设计规模是接纳五百名劳改人员。《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关押了三千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关在这里。右派们做梦也想不到,一进夹边沟,就像进了鬼门关,血色黄昏与死神一起,终于降临了——
仅仅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奴役劳累史;而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纯粹是三千右派的饥饿死亡史。在求生的渴望中,他们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或许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两千五百人成了饿殍!埋尸队忙不过来,将尸体草草掩埋,大风一刮,尸骨裸露于荒漠,至今无法认领……
极限饥饿下的灵与肉
人是万物之灵。人的道德、人的尊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然而,在夹边沟的极限饥饿下,却出现了好人学会了偷,人与老鼠抢食,人与猪同食,生吃牛肉,偷吃活羊内脏,吃粪便,甚至活人吃死人……
据幸存右派的讲述和杨显惠的调查,他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借此活命。1958年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不足7两,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不期而至,一批体弱不支者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少数老弱病残外,全部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恶劣,两千多名右派就打回原始人,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自此,死营右派们的活法儿,令人瞠目结舌、不寒而栗。
夹边沟的要命之处,除去超强的劳累和寒冷,更要命的是饥饿。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老右们就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一切可能保存热量,等待下顿糊糊汤到来。 如果还有点儿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洞,鼠口夺粮;偶尔看到晰蜴,抓住烧煮而食,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人吃树叶草籽,很容易胀肚和便秘,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儿,撅着屁股,相互配合着抠粪蛋。
人人皆知傅作义,却少有人知道傅作恭。傅作恭是国民党叛将傅作义的堂弟。他是留美博士、水利专家。中共建政后,傅作义任水利部长,写信叫弟弟回来为国效力。傅作恭放弃美国的优越条件和前程,欣然从命。
1953年2月,傅作恭任甘肃省水利厅总工程师。当时,甘肃省准备上马引洮工程,傅作恭经过考察,认为当时甘肃经济、物质、技术尚不具备上马条件。
以张仲良为首的中共甘肃省委,认为傅作恭的意见是阶级敌人向党进攻,傅作恭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
1960年冬天,饥饿到极限的傅作恭为了活命,支撑着来到场部的猪圈边,想找点猪食吃,却一头扎倒再没起来,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就在这年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的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于是,出现了最为惨烈的一幕:活人吃死人。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他们就划开胸腔,取出内脏……
极限饥饿,逼着人捉摸出不可思议的偷食绝技。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羊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这种偷技的精绝之处在于,羊当天看着没事,第二天才会死掉。
极限饥饿,催生出极限暴食。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等人,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得两眼发绿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偷偷把一麻袋洋芋煮熟,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吃个精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下,活活撑胀而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泻,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顾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因为极限饥饿,右派攻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科研课题“烧骨取食”——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场景:“……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在极限饥饿摧残下的肉体,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一位幸存的右派回忆道:“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待续)
夹边沟右派噩梦:吃死人 海归科学家活活饿死
957年,中共党魁毛泽东将55万大陆知识份子打成右派。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就是当时关押右派的一个劳改农场。在反右斗争中,夹边沟的右派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3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
夹边沟位于甘肃省酒泉市30里外,地处茫茫荒漠与戈壁之间,以沙土为主,地下水60%含碱,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常常是八级大风,环境非常恶劣。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夹边沟劳教农场约有3100名被打为右派的知识份子关押在这里,他们从事搬沙填海、挖排碱沟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此外还要忍受挨饿、辱骂和毒打,身体和精神遭受着双重的煎熬。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他们只是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而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拼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1959年开始,中国境内发生大饥荒,粮食定量急剧减少,夹边沟的右派们每天仅有半斤粮食,到最后为了活命,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体面人甚至吃老鼠、吃蜥蜴,吃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三年后3000人只活下来300人。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16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三位饿死的留美科学家
饿死的右派中有三位50年代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傅作恭、董坚毅和沈大文。这些爱国知识份子,他们为了报效祖国而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怀抱满腔热情回国后,却被自己的同胞当成特务,被咒骂,被毒打,被虐待,这其中饱含了太多的辛酸与委屈。
傅作恭,山西荣河安昌村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应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傅作恭的二哥)的劝说回国从事中国的水利建设。傅作恭回国后到甘肃省从事水利工作。
1957年受“反右”冲击,傅作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傅作恭由于身体弱,完不成劳动任务,有时连续几天扣饭。挖排碱沟时由于腿部长期泡于碱水中导致大面积溃烂。

1960年冬天,傅作恭因饥饿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董坚毅,上海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兰州,在甘肃省人民医院泌尿科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1960年11月上旬董坚毅在饥饿中去世,时年35岁。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发现裹尸用的毯子、羽绒被早已不见,董坚毅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
沈大文,留美博士,甘肃农大的教授,研究植物分类。1958年被打为右派后送到夹边沟农场,在农场期间,沈大文不偷不抢,饿得不行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因他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草籽都没有中毒。
1960年春,沈大文因饥饿失去行走能力,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自己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跪着去伙房。据其室友俞兆远回忆,有天夜里约11点钟时,沈大文说想吃个糜子面饼饼。他凭借关系弄来了两个,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伸手一摸,身体已经冰凉……
右派吃树叶、晰蜴、兽骨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著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贼骨头”的生存之道
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生性本分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
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吃呕吐物和排泄物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著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
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死亡高峰到来 活人吃死人
1960年9月,甘肃省劳改局计划在高台县明水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他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著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
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1960年11月中旬,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年10月,臭名昭彰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言论自由的压制从反右开始
在反右运动60周年之际,一部记录中国右派悲惨遭遇的影片《夹边沟祭事》,2017年2月25号在香港首次公开放映。导演广州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艾晓明强调,这不仅是一个历史故事,也是一个当下的故事。
这部记录片讲述1957年,50多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很多人死于非命。《夹边沟祭事》在香港首映,引起热烈反响。
影片聚焦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夹边沟劳教者遇害惨案,并追踪遇难者的后事处理。在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后,有三千多人被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他们当时被划为右派、反革命和反党分子等。
不过,就像文革一样,反右也成为敏感历史,艾晓明多次在夹边沟拍摄过程中遭遇当地阻拦和跟踪,并受到公安和校方的约谈。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他指出对民族精英全面打击的反右运动,却被定义为反右扩大化,还用封堵的方式截断这段真相的留存,说到底,中共是不会承认它的错误。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艾晓明老师拍摄这个影片,用这个东西(记录片)来比照今日,让大家觉醒,我们什么都没有变,国家的体制,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对社会精英的敌视,对社会思想精英的敌视,这一切的一切都还是在进行着,它是党性的核心部分之一。”
胡佳:“我爸爸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被打成右派,我妈妈是南开大学的学生,也被打成右派,他们一直到66年的时候才结婚,我们这个家庭的命运,就是他们两个是右派,然后50年之后,2007年,我又变成‘右派’了。”
夹边沟
“夹边沟”本为村名,因村子的一边为被当地人叫“边墙”的古长城,另一边是排洪沟而得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解放军第三军在夹边沟开辟了一个军垦农场,并于1952年兴建夹边沟水库,后因大坝坝坡渗流,存在严重隐患而将水库废弃。1954年3月[a],甘肃省劳改部门在夹边沟建立劳改农场,行政名称为“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对外称“国营夹边沟新建劳改农场”。农场的场部位于夹边沟村龙王庙原址,离夹边沟村约有二里路程。计划将夹边沟建设成为水浇旱田作物型的谷物农场,农作物以春小麦为主,并利用农场西面天然草滩发展部分畜牧业[2]。1956年7月,转为就业农场,除了安置的刑满释放的劳改就业人员,其他犯人大多被迁到马鬃山劳改农场[3][1]。
1957年下半年,随着“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4],夹边沟农场成为接收甘肃省各地“右派”分子的劳教农场,改称“酒泉夹边沟劳改劳教农场”。夹边沟农场接收的第一批劳教人员是1957年11月初甘肃省酒泉运输公司的4人、劳改局的4人和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的48人。此后直到1960年底,陆续有3千名左右的右派分子被送到该农场接收劳动教养,具体数据各材料稍有不同。夹边沟农场环境恶劣,劳教人员过多,农场无法自给自足。恰逢全国性的大饥荒,而且当时农场管教和上级部门按照“右派就是反动派”的逻辑,未给农场提供充足的粮食,致使在夹边沟农场的部分劳动教养人员因饥饿等原因死亡[5][1]。
1960年6月,中共甘肃省委成立省农垦委员会。成立当月,农垦委员会召开河西农垦会议,提出在河西走廊开荒四千万亩。9月,中共张掖地委按上级指示,提出再新建12处农场的目标,计划在高台县明水滩新建的明水河农场就是其中一个。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通知后,除留下少数人员留守外,将其他一千九百多人全部调往明水滩。由于粮食不足,明水滩几乎没有基础设施,大批劳教人员被冻死、饿死[6]:32。
1960年11月上旬,在甘肃河西地区检查工作的内务部部长钱瑛发现夹边沟农场和明水大河农场饿死人的情况。接着,中央派出检查团到甘肃开展“抢救人命工作”,检查团以钱瑛为团长,公安部部长王昭为副团长,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等参加。张掖地委派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马长义调查夹边沟和明水大河农场,至十二月中旬将在明水滩的劳教人员接到高台县抢救,夹边沟农场也同时开始抢救人命,并开始分批审查陆续将教养人员遣返[6]:32-33。
调往明水滩的一千九百多人仅抢救回二百多人,加上留守夹边沟的、在夹边沟下属石炭沟煤矿的,以及劳教期间逃跑的等,幸存者只有五百多人[6]:33。
1962年,农场改称“红星农场”,1968年由解放军接收管理,1974年改称“酒泉地区长城机械化林场”,1982年改称“酒泉县长城林场”,1985年改称“酒泉市长城林场”。2003年,改称“酒泉夹边沟林场”,为酒泉市肃州区林业局管辖的一个生态林场[7]。
劳教人员数量
根据甘肃省甘发(64)60号文件统计,原共有2369人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其中右派分子887人,反革命分子898人,坏分子438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68人,贪污、违法乱纪分子78人。据曾在1960年底中央工作组来后被抽到高台农场成立的一个临时办公室的幸存者腊静华回忆,临时办公室统计总人数有三千多,幸存者有五百多。1958年最高峰时,农场向劳改局汇报的人数为3074人,其中女性32人。据管教人员司继才日记记载,1959年11月发放冬衣时,共有3136人。由于农场中有一些因故未记录在案的劳教人员,因此作家赵旭估计总人数应在3500人左右。劳教人员中所有死难者均为男性,女性通常会被安排到一些劳动强度弱的岗位上,因而得以幸存。[1][6]:28
农场领导
1956年3月,刘振玉任夹边沟农场第一任场长[8][b],第一副场长为王德富,第二副场长为姚世虎,教导员为申有义。1957年反右运动后期,申有义被划为“中右”调往新疆。1959年,王德富和姚世虎调到安西马鬃山劳改农场。[6]:31
1958年底,升级为县级单位,张宏被任命为夹边沟书记兼场长,梁步云任副书记,刘振玉为副场长。1959年,张宏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改在农场赶马车[9]。原甘肃省金塔县县长张和祥被任命为场长,但因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分子未就任既被撤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张宏被打倒后,农场主要由刘振玉领导,但由于刘振玉党籍一直未被恢复,所以职务为副场长。[6]:31
科室情况
夹边沟农场最初为科级单位,1958年人数增加到三千多后升级为县级单位。下设管教股(对外称教育科)、财务股(对外称财务科)、生产股、秘书股和医务所等,生产股下辖场部的三个大队。[6]:30
分队情况
1958年5月之前,全场为一个大队,10个小队。1958年6月,划分农业队、基建队、副业队;同时开始建新添屯作业站。大队长、教导员、中队长、指导员有农场管教干部担任;大队和中队的文书、统计、管理员、粮秣、司务员、上士、小队长和班长等从劳教人员中选任。
杨显惠:触目惊心:夹边沟右派的千种死法
1958年前后有数千名右派被发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两三年期间,大半数人仅剩一把骨头,埋在了农场外的荒野。
作家杨显惠,1946年生于兰州,1965年上山下乡,1988年入天津作协专职写作。他跟踪采访夹边沟幸存右派多年,并于2000开始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开始连载,并结集出版,那些故事中的主角与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他们有他们的故事,和他们面对命运和面对死亡的姿态。本文节选自《夹边沟记事》。
1、冻
1960年冬,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吃,倒在了猪圈旁边。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他的尸体覆盖起来了,好几天都没有人发现他。于是人们传说他逃跑了,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给哥哥写过信,要钱。
到了春天,雪化了,尸体暴露出来,关于他逃跑的传说不攻自破。
他是右派,他叫傅作恭。在兰州读中学,金陵大学读农林系,毕业后在兰州搞农林试验站,意图走科技救国的道路。解放后,任甘肃省农林厅工程师。他是傅作义的弟弟。
2、睡
这可能是所有右派最常见也最悄无声息最平静的死法。他们在饥饿中疲惫地入睡,然后再也没有醒来。他50多岁,由于无力交谈,他始终未曾说过自己的身世。曾有两次,他不说话了,睡死过去,医生人工呼吸,打葡萄糖,把他救活了。他确实多活了两天,但是第三天夜里,他拥着被子坐着,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他是右派,他叫蔡子贺。
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
他是右派,他叫董建义,上海人,医生。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愿来到兰州,任省甘肃省人民医院泌尿科主任。
3、胀死
黄茅草籽煮出来的“粉汤”就像观音土,没有营养没有热量,但是能够将胃撑饱,消除饥饿感,吃上一次能顶三天。只是这种“粉汤”万万不能热着喝下去,必须要等着凉透了,切成小块服下。
他饿得受不了,实在熬不住饥饿,热着喝了半碗。结果胃里所有的柴草杂物被热“粉汤”粘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大的硬块,堵在肛门。不但拉不出来,掏也掏不出来。即使用上了专用工具,结果也是他的肛门被搞得鲜血淋漓,一塌糊涂,那个硬块却安然如初。他的肚子越来越大,五六天之后就胀死了。
他是右派,他叫文大业。甘肃省卫生学校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
4、吸烟
他在1960年春天临近的时候躺倒起不来了,奄奄一息之际对身旁的人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我想吸支烟。
好友从别的右派处要来一撮旱烟末,卷了颗烟,点着,放在嘴巴上。他用干枯得树枝一样的手指抖抖索索扶助了烟,吸了几口,闭上了眼睛。
他是右派,他叫巴多学,永登县人,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永登县一中教师,胆小本分。
5、糜子面饼
他丧失行走能力已经很多天,但他不愿意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去伙房打饭的路都是跪着走去,再跪着回来。
某子夜,他说他想吃个糜子面饼子。同屋的好友求爷爷告奶奶终于要来了两块,高高兴兴地给他吃了。翌日清晨,他静静地躺着不动,头已经冰凉。
他是右派,他叫沈大文,甘肃农大教授,留美博士,专门研究植物分类。
6、撑
他们被外派出去装车,装的是洋芋。连续两天劳苦,看管他们的头头一时豪迈,让他们挑了一麻袋洋芋,足有160斤,煮了满满一大锅。他们不等洋芋煮熟就开始吃。大家都知道今后再也不会有机会这样可以饱吃一顿的机会,结果呢,洋芋都吃得顶到嗓子眼儿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也坐不住。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了,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地往下咽。结果回程的车上,一车的人都痛不欲生。他的胃太胀了,颠得太疼了,最后胃被撑破了。被人扶到宿舍后,半夜里就断气了。他是右派,他姓吴,来自天水。
他妈给他寄来了两斤炒面,一斤白糖。他吃了一斤炒面,半斤白糖。心里饿,没忍住,就把剩下的也都吃了。胃疼,犹如刀绞,还胀,胀得坐不住。后来他不再喊叫,卧在床上轻轻呻吟。当晚十点钟,他的嘴角流出一点黑色的血液。他死了。他是右派,他叫李汉祖。转业兵,甘肃省公安厅二处内勤。时年29岁。
7、断肠
他是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招待所哪敢怠慢呀!叫他住最好的房子,一天三顿,伺候他吃好,吃饱。但是,三天之后他死掉了。他的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肉,不消化,食物把肠子挣断了。
他是右派,他叫王玉峰,山东人。国民党运输局星星峡转运站站长,期间利用职务和专用站地利条件,多次营救逃亡中的共产党人。解放后,因为口碑良好,被酒泉军管会调任后勤部工作。后辗转于省交通部门。1957年被打成坏分子,被送到夹边沟劳改。
1960年在劳改农场偶遇曾救过的共产党人常子昆,被从劳改队救出。没想到,却因福得祸。
8、肿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是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梨,里面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是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斋得开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
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出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蓄积力量和保持平衡,再把另外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他是右派,他叫牛天德。他是他们中的一员。解放前是东北一家工厂的工程师,建国后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建设,从东北到兰州,任省建工局工程师,时年近六十,一派儒雅书生的样子。
9、狼
他在生命最衰弱的关头,焕发出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和他的年轻徒弟,乘着夜黑风高,逃出夹边沟农场。只是,逃不过两里路,他就走不动了。徒弟搀着他走,扶着他走,他还是走不动。徒弟背着他走不过百多米,两人都走不动了。后来,他拒绝让徒弟背着,并坚决地赶走了徒弟。他披着徒弟执意留下来的棉大衣,在寒风中等来了同样饥饿的狼。令人错愕的是,饿狼将他吃得干干净净,就留下了个棉大衣。后面来追逃的劳教队管教看着大衣,以为是徒弟被狼吃了呢。而他,他不翼而飞。他的徒弟因此才得以逃脱。
他是右派,他叫骆宏远。三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解放前就是土木建筑行业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初内部肃反,被下方当了工人,木匠,后被从东北调任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1958年秋,白银公司在反右斗争中老账新算,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扭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浇水的时候,狼不敢吃人,它看见他们手里拿着铁锹。狼就吃浇水睡觉的人。狼吃人,先要弄清楚死人活人。它会给他们脸上泼水,叫他们在睡梦中翻翻身子,等他们裹着的皮袄散开了,脖子里也没有挡挂了,它一口就咬住他们的要害,置他们于死地。他们是右派,他叫两三个右派。
10、绑
半夜时分,他撬开了伙房菜窖的门偷胡萝卜,被炊事员抓了。麻绳打在肩膀上,麻绳缠住两臂,麻绳系住手腕。接下来就听见肩头骨节发出嘎巴声,肘关节发出嘎巴声,他的双手从背后上拉倒了后脑。他没有喊,没有哭,没有求饶。
他只是不断地咧着嘴,像抽风一样,嗓子里发出不由自主的嗷嗷声。他的身子被麻绳勒得变了形:他的腿可怜地蜷着,腿就像是短了半截;他的腰弯着,肚子就要触到膝盖了;他的头被麻绳扯得奇怪地仰起;后背上的双上和胳膊如同驼峰……然后就是暗黑的菜窖。天亮以后,他在菜窖冻成了冰块。
他是右派,他叫一个右派。
11、心力衰竭
她雪夜奔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夹边沟,探望她的右派丈夫。
农场的工作人员翻出个花名册,翻了几页说,他死了,死于心力衰竭。
他是右派,他叫王景超。河北农民出身,为人正派,不卑不亢。战乱中依靠打工挣钱考上西北大学哲学专业。西安解放后,随团来到兰州,创办甘肃日报。后因写杂文论政,被打为右派。
12、想孩子
他给老婆写信说他想孩子,想见见孩子。她接到信之后,带着14岁的男孩和8岁的女孩,长途跋涉一千公里来到农场,却没有见到丈夫——他在十天前就去世了。
估计是因为太想孩子了吧。掩埋丈夫的人也去世了,她没有找到他的坟头。
他是右派,他叫一个右派,来自天水。
13、发烧
她和他们五岁的孩子到农场的前两天,丈夫就躺倒在一个只能住两个人的窑洞里,发烧,说胡话。
她和孩子在守了十天,天天把炒面用开水冲成糊糊喂丈夫,但他始终没有醒过来。
他是右派,他叫一个右派。
14、衰
从夹边沟到明水农场的时候,在火车上,他被贼娃子偷了一次。贼娃子把他的行李解开了,把钱、粮票和几件衣裳都偷走了。后来他写信跟家里人要吃的,家里从邮局邮来了十几斤炒面,当天就被贼娃子偷走了。他把包裹挂在墙上,把一件呢子大衣盖在上头出去解手,回来,连大衣带炒面都不见了。他一下子就哭开了。
他的情绪一直不好,身体虚弱得很,已经出现了一次休克。护理员叫大夫抢救过来了。大夫叮嘱护理员,不叫他睡觉太死,过一会儿就叫醒了说几句话。那天晚上,护理员也不小心睡着了,发现时已经晚了。大夫打强心针,人工呼吸,也没有抢救过来。他是右派,他叫赵庭基。永登一中教导主任,在台湾上的大学,解放后任中学教师。
他是有一箱子炒面来的,能顶一气的。可是叫人把炒面偷掉了,就饿死了。他是右派,他叫王朝夫。临洮县人,临洮农校毕业,县农业局干部,时年22岁。
15、躺着
如果能够的话,他总是静静地躺着。他知道漫山遍野地奔走挖草根撸草籽儿,消耗的体能远不是那点草根树皮草籽儿能够补充上来的。所以他总是静静地躺着。他总是抱定活下去的希望——家里人还等着他回去团聚呢。他深知如果连活的欲望都没有了,精神就垮了,那就死定了。
很多身体比他好的,到处找吃的的,家里隔三差五邮寄点食物来的……都死了,他一直活着。一天,他拉着垂在胸前的绳子想坐起来,但使了使劲儿也没有坐起来。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他把手表交给护理员,作为女儿未来的结婚礼物。翌日黄昏,他闭着眼睛静静地躺着,身体已经没有了体温。
他是右派,他叫张继信。西北师院学历史,毕业后考上北大学中文,后续修北大英语系毕业。
16、抖
晚上睡下以后,他不停地发抖,说冷。早晨起床的时候,人们发现没气儿了。
身体热量不够的时候,就会降温,温度降到35度的时候,身体就会发热出汗,出汗带走热量就会发抖。这时候,如果补充不上热量,人就会死。
他是右派,他叫高怀德,甘肃武威师范老师。
17、感冒
他一来劳改农场就当了卫生所的大夫。他给他的熟人开病假条,没病的也开。领导知道了,下放到农业队劳动。得了一场感冒,就死了。他来农场就当大夫,没受太多苦,身上还有肉。死后被埋他的饥饿的右派盯上了,屁股上的肉被剁了一块,煮着吃了。他是右派,他叫刘峰山。
他也是刚来到夹边沟农场劳教就被任命为医生,没受太大的苦。在医务所期间,他又有新的言论——他说夹边沟死亡那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便被撤掉了医生职务,下生产队劳动。后突发感冒,就死了。
死后,因为身上还算有肉,两个屁股蛋子都被人用刀子剜去吃了。他是右派,他叫王夷悟,天祝县医院医生。
18、毙
她黑黑的,典型的南方人,在夹边沟先后种菜,算是夹边沟幸存的右派之一。从夹边沟回到兰州之后,与另外一个右派结婚,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老师,就把他们下放到静宁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外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都见不上两面。
“文革”当中两口子被揪了出来,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
她是右派,她叫毛应星。毕业于西南林学院,学林果和蔬菜专业。
19、晕
他心力衰竭晕厥不醒。新来的大夫,给他打了强心针,推了50毫升葡萄糖,后来又推了100毫升,他还是没有醒转过来。
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晕厥三次了,就算是再多葡萄糖也救不回他的命了。
他是右派,他叫一个右派。
20、等不及
他一直在炕上躺着。身上除了被子,还压着一件狐皮领子的大衣。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似乎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谨慎地请支援抢救的军队卫生队医生帮他给身为团卫生队队长的女婿带个话,要点炒面和糖。女婿女儿偷偷摸摸委托小军医大包小包给他带了不少珍贵的食品,小军医刚刚赶回农场,他却晕死过去。医生抢救半天,还是没有活过来。
他是右派,他叫吴成祥。内卫72团卫生队队长季自生的岳父。
21、拉
他肠胃不好,经常生病。1960年夏季,他在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工作站肠胃病突发,一连多日泻肚,什么药也止不住,立即就被放倒了。医生看他可怜,就电话向上转院。却被夹边沟厂部卫生所所长直接拉去了农场旁边的炼钢厂,也就是医院的太平间等死。
炼钢厂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1959年被改造为医院的太平间。都是他随身携带的铁皮箱子里的金表金项链玉石镯子国债券惹得祸。
他是右派,他叫贺秉灵。上海人,解放前跑去台湾工作,在一家公司任会计。五十年代中期跑到香港,通过朋友从香港跑回广州,想回去上海和家人团聚,却被人安排到了玉门油矿工作,家人一个也未见到。工作一年多之后,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
22、治
他来劳教农场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肝炎。住院半年又回来了,肝炎转为肝硬化。后来病情加重,我给厂部医务所所长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所长不叫送。
死前,他叫所长来见面。所长爬上炕坐在他身边。他就去摸所长的手,摸所长的胳膊,摸到所长的脸上了,就狠狠地抓了一把。所长惊得跳下炕去。半小时后,他就烟气了。弥留之际,孱弱如他,心中对于眼前这个将他的肝炎治成肝硬化的医务所所长,对于这个如此残酷对待他脆弱生命的世道,该有多少无法释放的愤恨啊。
他是右派,他叫天津青年,演员,敦煌县文化局干部。
23、中毒
有一天,在挖野菜回来的路上,他打了20多条蜥蜴,点火烧着吃。蜥蜴表面烧黑了,但里面还没烧透,咀嚼的时候,咯吱咯吱的。过了两三天,他的身体突然肿起来,全身都肿了,像是吹起一样,肿得像是水缸一样粗,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医生说是洗衣中毒,给了几个白色的药片,就走了。
过了一天,他就完全闭上了眼睛。他的皮箱里,他用大学女友分手时送他的浪琴从南寨村换来的炒面还有两三斤,白面饼子还有两块,干得掰都掰不动了。
他是右派,他叫邹永泉。复旦大学数学系55年毕业,他是班上的团支部委员,毕业时相应国家号召,毕业就带头报名支援大西北建设。结果到了兰州后,分在兰州一中教数学。
24、拒绝吃药
他奄奄一息,但仍然拒绝打针吃药。他说他得的是空肠病,打针吃药没用,还不如一碗面汤顶用,节约下来药片给有用的人吃。
他的家人通过邮局给他寄来了几斤熟面,但已经晚了,无济于事,吃完那些熟面以后,他就告别了人世。被褥底下是大把的药片。
他是右派,他叫石玉瑚。
25、兴奋
1961年1月31日傍晚,大广播里吱吱扭扭地开始讲话,天亮之后右派就可以回城了,汽车明早来接。当晚大家都很兴奋。他也是。
他整夜跳进跳出,说呀说,笑呀笑,唱呀唱,折腾补休。天亮了,汽车来了,临上汽车,他却一个跟头栽倒了。几个医生围着抢救半天,也没能醒转过来。
他是右派,他姓陶,部队干部,军校教师,1938年参军的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