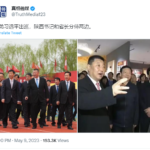2月23日, 武汉封城一个月整。
一个月前,杨晶晶和很多人一样,在朋友圈中转发了官方那句充满正能量的口号“武汉加油”;
一个月后,这位28岁的武汉房地产销售员说,她的世界崩塌了。
两天前,警方通知她,有人在路边发现了她父亲的尸体。人已经去世几天了。
51岁的杨元运是武汉嘉华汽车塑料制品公司的员工,杨晶晶一家的顶梁柱。
2月16日那天,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给家人做饭。他没带手机也没带钱包,一声不响地离家出走了。
临走前,他在手机上给妻子写下最后的留言:
“我走了,不能陪你到老了,无处可逃。”
他没有按下“发送”,这封留言至今还躺在他微信的草稿箱里。
那天,杨元运还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几行遗书:
“我爸那么好一个人,真的一心一意为我家,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武汉女孩杨晶晶的爸爸16号离家出走。她说,封城后不让家属出去找,只能在家守着等消息,这是最难过的。2月21日,晶晶发了一条微博,“警方通知我爸爸找到了,但是爸爸已经去世了。” #武汉 封城一个月了,听听武汉城里人的故事。 pic.twitter.com/97lsCkz1J4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February 23, 2020
“如果这次疫情和我开了一个玩笑,我坦然接受它的洗礼。如果我的病体有用,就献给这次疫情做医学研究。愿天下人不受病魔的折磨!”
“他一直瞒着我,不跟我说他的身体状况,也瞒着我妈,” 2月20日,被隔离在武昌的杨晶晶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我只想找到我爸爸。”
此时的杨晶晶还不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人间。
杨元运失踪几天后,母女二人才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一连几天,他通过微信联络社区人员,报告自己发烧、胸闷,哀求他们安排他就医。
但社区一直推诿说没有床位,态度也很冷漠。
“我觉得你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病,就是你想太多了,知道吧。” 汉南区纱帽街薇湖路社区一位工作人员回复他。
几天来,美国之音多次致电该社区,但电话无人接听。
“我妈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爸在跟社区求助,”杨晶晶泣不成声。“我打电话去社区问责,他们说我是骚扰他们。他说,我们100%没有责任,你们作子女的干嘛去了?”
中国官方数字说,截至2月22日24时,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6936例,累计死亡病例2442例。
倒在路边的杨元运不会被纳入这些数字。像他这样没有确诊,甚至连医院的门都进不去的非正常死亡者在中国大地上不知还有多少。
这场举国大疫中,很多人死了,却连一个数字都不是。
武汉作家方方在她广为流传的《封城日记》中写道:
“武汉现在是在灾难之中。灾难是什么?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
这篇日记不出意料地被官方删除。
武汉封城一个月之时,美国之音联络了这座孤城中的普通人。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里,他们往往渺小如尘埃,我们希望记录“尘埃们”的声音。
51岁的武汉钢铁公司前消防员徐武在电话中哭了。
2月4日,他的父亲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社区说没有床位,也没有车。徐武用轮椅推着80岁的父亲辗转了附近的几家医院。每家医院都说,病情很严重,但资源有限,无法收治。
2月14日,武汉下起了大雨。回家的路上,父亲的病历不小心被遗落在雨里。
晚上,徐武看到父亲在房间一角艰难地吃菜苔。他已经不能吃饭,吃了就全吐出来。
“想起来就难受,”徐武的声音哽咽了。“我那天半夜搞到凌晨1点钟,联系了很多人,我觉得父亲不行了,我就发帖了。”
两天后,终于有一家医院收留了父亲,徐武松了一口气:“在医院抢救比在家里等死要强。”
他不知道,在这场疫情中,他们一家会不会经历生离死别,但他相信,如果不是那天上网求助,父亲此时已经不在世间了。
25岁的浙江小哥楼威辰在武汉做志愿者,日日奔波在大街小巷,给有需要的人运送物资。一个月来,他目睹了这座悲情城市中一幕幕人间惨剧。
51岁的武汉钢铁公司前消防员徐武在电话中哭了。2月4日,他的父亲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社区说没有床位,也没有车。徐武用轮椅推着80岁的父亲辗转了附近的几家医院。每家医院都说,病情很严重,但资源有限,无法收治。 #武汉 封城一个月了,听听武汉城里人的故事。https://t.co/wU7p0mrPJm pic.twitter.com/OuR3f1sZQ4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February 24, 2020
“我救助了一户家庭,这户家庭本来是四口之家,还蛮其乐融融的,结果肺炎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母亲也因为肺炎进了ICU,后来姐姐也进了医院,被列为确诊病人,弟弟在酒店隔离,”他告诉美国之音。
真实世界的残酷让这个年轻人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有很长时间我都在失眠,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他说。
封城后不久的一天,90后办公室白领辰辰去医院给姨妈送饭。姨妈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生,1月中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家医院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两公里。
辰辰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晚上5、6点,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好像生化危机的电影。医院门口全是救护车、警车,特别紧张。整个医院特别安静,好像没有人一样。”
几天后,辰辰的姨夫也被确诊,妈妈被诊断为高度疑似。辰辰顶不住了。
“2月初的时候,特别郁闷,有点怀疑人生,”她说,“每天打开头条,打开微博,发现死亡数字一天天攀升,后来我干脆就不看了。”
在武汉土生土长的辰辰说,她和这座城市中的很多人一样都很愤怒。12月底,朋友圈就开始流传肺炎的消息,人们半信半疑。但是到了元旦,政府特别发了一条新闻,说是谣言,还把那八个“造谣者”抓起来了。 当时大家拍手称快,觉得政府办事效率很高,放心大胆地出门了。
“明明是可以控制的,却搞到现在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 辰辰对美国之音说,那时候她和网友天天在微博上大骂湖北官员。“我们还给市长啊,书记啊,省长啊起了外号,叫‘湖北F4’,天天都说他们怎么还不下台。”
2月14日,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被免职。这则消息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人们说政府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但辰辰觉得没那么简单:“这个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谁又知道谁要把这个事情压下来的呢?也不可能他们四个把这个事情压下来吧。”
辰辰说,但这种事情,“我们这种小市民是不知道的”。
封城一个月后, 武汉依旧如末日电影般死寂,期待的拐点没有到来,各地赶来的医护人员还在一线冒着生命危险救治病人。
但是,不少百姓已经摆脱了最初的恐惧和无助。他们热络地讨论着哪家的团购物美价廉、畅想着解封后把火锅、热干面吃个够。
武汉市民“涛鸡公”每天都在YouTube上直播他们的封城生活。世界各地数万观众守在屏幕前看着这一家三口买菜、吃饭、侃大山的日常。灾难太过惨烈时,这样的人间烟火格外令人动容。
在武汉之外,为了挽救经济,中国很多地方开始复工。当局几次调整统计标准,使新确诊数字大幅下降。2月22日,北京、上海、浙江等多个省市均通报零确诊。
各地一些商家也陆续营业,在家憋得太久的人们一窝蜂上街了。口罩不戴了,该吃吃,该喝喝。
于是,民间有人大声疾呼:“各位,疫情还没结束啊”,“好了伤疤忘了痛吗?”
中国作家阎连科撰文反思说:
“我们作为人———我们千千万万的百姓或蝼蚁——我们自己太没记性了。我们的个人记忆被规划、取代和抹杀了。我们总是人家让记住什么的就记什么,让遗忘什么的就忘什么;让沉默时沉默,让歌唱时歌唱。”
立春已过,现在已是早春。只是不知道疫情结束后,在官方奏响的凯歌声中,在这个国家准许流通的恢弘叙事里,谁会记取这些普通人在这个冬天里的绝望、痛苦、生离死别。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辰辰为化名。
——转自《自由亚洲》
(责任编辑:云涛)